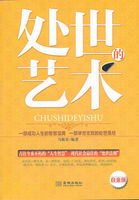两年之前,我的女儿曾经在一所管理严格的寄宿高中读书。星期天,我从南京坐汽车去看她。同宿舍的女孩子们都回家了,因此我们有一个母女独处的空间。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房间里光线很暗,敞开的气窗里飘进来厕所和盥洗室淡淡的异味,几架双层床铺上的被子叠得军营一样整齐,牙杯牙刷和饭盆脸盆在靠墙的木架上排列成士兵的阵势,女儿背后窄小的书桌上全是教科书和练习册:数学的,物理的,英语的,政治的……它们全都卷起了边角,封面被手指摸得毛毛糙糙,一本摞一本沉甸甸地堆积在文曲星和计算器旁,让我感觉透不过气的压抑,只有窗外飘扬的女孩子们五颜六色的胸衣内裤,给这个暗淡的冬日带来些许亮色。女儿十五岁,介于孩童和成人之间,轮廓尚未成形的脸上既有稚气的懵懂,又有过于成熟的冷漠,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神情组合。当时她很不在意地看着我,跟我说话的声调也是似是而非、没有丝毫感情色彩的。她告诉我说,她想写这样一篇作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便是:主人公早晨出门,一抬头,看见了落在树上的天使……她接着又说,不行的,不行不行,老师肯定要说她胡编乱造,判她“不及格”……作文不可以这样写。哪里能够这样随心所欲啊。
女儿就这样自言自语着。她脸上的皮肤在幽暗中泛出一种毛茸茸的透明,目光越过我的头顶,不知道投向了天外的什么地方,显得那么空洞又那么渺茫。她的身体坐得笔直,穿牛仔裤的双腿微微地并拢,显示出处世不惊的沉稳,与她十五岁的年龄很不相称。
可是,就在那一刻,我被女儿深深地感动了。我认为在那一瞬间我已经触摸到了她的灵魂,一个渴望高高飞翔的灵魂,一个身处凡俗和压抑之中、却又从平地腾空跳起、自由自在飘扬舞动的灵魂。那一瞬间里,她的人性和人格是分离的、矛盾的、裂变的。她在今天和未来之间,在现实和梦幻之间,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摇摆,寻觅,和冲撞。
两年过去了。如今我的女儿已经在国外的学习生活中游刃有余了。她肯定忘记了十五岁的那个冬日,她在一间阴冷却又整洁的高中女生宿舍里对我说过的话——她想像之中一篇作文的开头。世界是一个千变万化的魔筒,时刻幻化出五颜六色的镜像。而孩子的心灵永远是个漏斗,不断地填充进新的事物,然后一点也不可惜地淘汰掉不那么新的东西。她能够在一天当中冒出十个念头,睡一觉之后又统统将它们忘光。有什么关系呢?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可以继续构建,继续梦想,继续忘掉旧的召来新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生命化蛹成蝶而后一飞冲天的过程,她必须这样选取、舍弃和建设。
可是我,我不是女儿,我是母亲,所以常常弯腰曲背跟在孩子的身后拣拾垃圾。我愿意珍藏她的每一个笑容,每一步脚印,每一句有口无心的呓语。“主人公早晨出门,一抬头,看见了落在树上的天使……”真的是一个好美的作文开头啊,两年中这个简短的开头始终在我心里盘旋,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经意中的一个抬头,眼面前就好像跳出一个长翅膀的天使,有一点像拉斐尔笔下漂亮的安琪儿,但是没有那个时代的红润和健康,它应该是柔弱的,敏感的,苍白和忧郁的,就像一棵过于美丽的极品玫瑰,本来应该开得人见人爱香气扑鼻,可是一不小心被人栽到了高楼之下的瓦砾堆里,先天生长不足,后天缺水少肥,它就那么瘦茎茎地在世上孤独挣扎。这样,这个柔弱无助的孩子碰到他生命中的守护者——顽劣、皮实、善良而且忠诚的男孩单明明。像正负电荷的相引相吸,像天空和大海的相配相衬,像黑夜和白天的相包相融,这是一种心灵和心灵之间的相互守望,是人世间最最无私无欲单纯朴实的友谊,它只能存在于童年之间,在互助、互补、互吸的两种性格之间。
但是,生命永远无常啊,柔弱多病的杜小亚终于因为不可抗拒的命运劫数随风而逝。他死后变成了一个小小天使,只存在于单明明的听觉和视觉之中。两个孩子的角色忽然间发生逆转,杜小亚反过来成了单明明的守护者,它忠实地伴随好朋友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来来往往,影响、帮助、改变着单明明的一切,使他不断地较正生活轨迹,朝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奔跑,最终他的灵魂在跑道上高高地飞翔起来,他触摸到了天使杜小亚的身体,他的生命可以到达一个自由无羁的状态。
就这样,我写完了我的第三本儿童长篇小说《我飞了》。最后一天在电脑上点击了“存盘、拷贝、打印”字样的时候,我坐在冬日的窗前,心中感受着一种无边无际的纯净和光明。我忽然很舍不得离开我的两个孩子:单明明和杜小亚。他们像我笔下无数的人物一样,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且哭且笑地陪伴我三两个月之后,倏忽而去,从此便无影无踪。我心里留下来的全都是快乐,那种带着忧伤带着想念带着祝愿的快乐,就像两年前我在机场告别我女儿的时刻一样。有一首我最最喜欢的歌,歌者是莎拉布莱曼,歌名就叫《告别的时刻》,每次听这首歌,心里涌出来的就是这种海潮一样淹没我头顶的情绪。
我的孩子们就这样一个个地离开了我,从金铃,到肖晓,到杜小亚和单明明……他们的姿态是这样的:手一松,就像鸟儿一样扑簌簌从我身边飞起来,眨眼间不见了踪影。我永远都不知道他们最终会飞到谁的家里,和哪一个爱读书的孩子结为好友。因此,这也是写作对我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