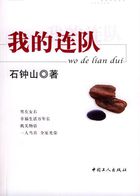是一架牛车,拉车的却不是牛。一开始,好古将其错看成了一头黑色的牛。不过没有这种椭圆的牛,分明不是牛的样子。虽说有月光,终究是晚上,实在难以看清。但那绝不是牛的动作,它的腿要比牛多得多。
车在庭院中骨碌停下。好古才看明白那究竟是何物。一刹那,他差点尖叫起来,全身寒毛竖起。
那竟是一只牛一般大的乌黑的巨型蜘蛛!车内的主人竟然把轭架在了蜘蛛的身上,让它拉车。黑暗中,蜘蛛八只红色的眼睛发出恐怖的妖光。
乘车者从车子后面下来,走过庭院登上台阶,站在外廊上。
那是一个女人,身披唐衣,罩着绸纱的斗笠。由于背对月光,尽管看得清她的白纱斗笠,她的脸却笼罩其中,看不分明。但白皙的下巴和血红的嘴唇依然可见。
“好古大人!”那嘴唇动了,“东山的云居寺有东西寄存在你这里,对吧?”跟刚才黑影所问的话如出一辙。
“不,不知道。真是莫名其妙。”
“如果隐瞒,对你可没有好处啊……”女子的嘴唇轻轻一抿,露出白色的牙齿。好古看作女子在微笑。
“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你说,我究竟为云居寺保管了什么?”好古问道。
女子并不作答,似乎在斗笠的薄纱后凝视着好古的一举一动。
“那我就只好自己查找了。”女子说道。
倏的一下,女子的身体动了,仿佛被风吹拂着一般。她走向外廊左侧,停下来,抬头看看屋顶,又低头看看地板。
“不是这里……”女子喃喃道,又走了起来,一时又停下来,嘴里念叨着与刚才一样的话,“也不是这里啊……”
女子在府邸中静静地走来走去,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也不是这里啊……”好古好几次听到同样的声音。
不久,女子返了回来,跟刚才一样站在木地板上。
“似乎的确不在这里……你很幸运。”女子笑了。
“我本来想,如果你撒谎,就把你抓来吃掉。”她忽然说出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从斗笠后面注视着好古,“虽然不在这里,可是,你有没有把它藏到其他地方?”
“不知道。”好古答道。
“一旦发现你在撒谎,我们还会来的……”说完,女子转过身去,钻进牛车。
嘎吱—骨碌—
牛车动了。蜘蛛的八条腿也纷纷动起来。黑影们收起刀,用绳子将好古的手脚捆起。
“如果用牙齿来解就太费事了,等到天亮之后,让你最先醒过来的随从来解吧。”说罢,黑影下到庭院里,朝女子所乘的牛车追去。
角落里的影子也都动了起来,下到庭院。
嘎吱—嘎吱—骨碌—骨碌—
车子的声音越去越远,人影也看不见了。夜色中,只传来那渐行渐远的嘎吱声……
“天亮之后,好古大人就被醒来的随从给救了。”博雅说道。
“唔。”晴明将手指按在下巴上,“奇妙极了。”
“喂,晴明,都这时候了,你居然还说风凉话?”
“这又有什么关系?最终谁也没有受到伤害,什么东西也没有被盗走,不是吗?”
“倒是这样。”
“有一点让我很感兴趣。”
“怎么,晴明,你发现了什么?”
“不,我不是说发现了什么,只是说,这里面有点东西让我很感兴趣。”
“好古大人所讲的那位罩着斗笠的小姐,她究竟在找什么呢,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唔。”
“从那以后,好古大人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或许一旦有事发生,就会把你叫去。”
“唔。”晴明把视线投向庭院里的樱花。
“喂,晴明,你到底听见我说话没有?”博雅说道。
“你的话或许还没有讲完,不过,待会儿再说吧。”
“什么?”
“有客人来了。”晴明说道。
听他这么一说,博雅也把脸转向晴明视线所指的方向。那里是樱花树。月光下,一瓣,两瓣,花瓣在轻轻地飘落下来。
树下似乎有东西。黑黢黢的一头兽。
一头黝黑的老虎盘踞在绽放的樱花下。似蓝似绿,不,金绿色的两只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晴明与博雅。
黑虎的背上横坐着一个男人。男人微笑着,看着两人。
“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保宪大人?”晴明说道。
“好久不见,晴明。”骑着黑虎的男人—贺茂保宪说罢,笑了。
黑虎驮着保宪,缓缓从樱花树下出来,走到外廊下面,止住脚步。
“一定是有要事吧,保宪大人?”
“嗯。”保宪点点头,从虎背上下来,“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啊,晴明。”
月光下,道满悠然前行。他肩上搭着一个皮袋,袋口用绳子扎住。皎洁的月光投下他的影子。
忽地,道满止住脚步。眼前是一个大池塘,池畔有松树和枫树。
道满驻足的地方生着一株老柳树,刚刚长出新芽。柳枝摇曳着,轻轻拂在他肩上。静谧的水面映着月亮的倒影。
道满从肩上放下皮袋,解开袋口。一个粗大的黑东西蜿蜒着从袋中游出。道满用右手抓住它。
“别闹。”他蹲下身子,将手中的东西轻轻放入水中。甫一放手,那东西便向水中央游去。它蜿蜒前行,水波缓缓蔓延开来。
这时,映在池塘中央的月影忽然碎裂了。水面隆起,波浪翻滚。似乎有巨大的东西在水下游动。
啪的一声,有东西的尾巴击打水面。
“好了,我给你带饵食来了……”道满微笑着说。
水下,那物朝道满投放的东西游去。
“啪—”水面激起一团剧烈的浪花。忽然现出一个怪物,一下将游在水面的东西衔入口中。
月光下,一条巨蛇般的怪物昂起头来。
“哦,香不香,好不好吃?”道满的唇角翘了起来。
蛇状怪物将衔在口中的东西吞下,便将身子沉入水底。水面剧烈地波动了一阵子,不久静下来。池塘恢复了当初的平静,只留下月亮的影子。
三个人在饮酒。晴明和博雅,外加保宪。
一只黑猫蜷曲在保宪身边,正在酣睡。保宪骑乘而来的黑虎的真身便是这只猫。它不是普通的猫,是保宪用作式神的猫又。
“最近,净出些怪事……”保宪将酒杯送到嘴边,说道。
贺茂保宪是晴明的师父贺茂忠行的长子、晴明的师兄,历任天文博士、阴阳博士、历博士,还当过主计头,现在担任谷仓院别当一职,官位从四位下。
“不错,似乎又出乱子了。”晴明点头应道。
“小野好古大人的府邸进了贼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
“若说这件事,刚才我还在和博雅谈论呢。”
“据说是不偷东西的盗贼。”
“哦。”
“那么,最近女人频频遇袭被杀的事呢?”
“听说了。听说专杀怀孕的女人,光这个月就有八人遇害了。”
“是九人。”
“哦?”
“今天中午,发现了第九个遇害者。”
“地点?”
“鞍马的山中。”
“鞍马?”
“是宫里的女子,因为怀了孕,就回到了贵船的家里,两天前却不见了踪影。”
“那……”
“是一个进鞍马烧炭的人在山中发现了女子的尸体。”
“果真如此,也是怀孕了?”
“嗯,惨不忍睹。肚子被剖开,里面的孩子被揪了出来。”
“那,孩子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
“男孩的肚子上有没有伤?”
“有……”保宪意味深长地注视着晴明的脸。
“是这样?”
“真是不吉利。”
“在宫内歌会即将举行的当口,竟频频发生不祥之事。”博雅说道。
“那么,今晚你大驾光临,为的就是此事吗?”晴明问道。
“不,不是。”保宪把酒杯送到嘴边,再放回木地板。
“那是为何事?”
“你认识平贞盛大人吧?”
“不熟,也就是见了面打打招呼而已。”
“这是一个与忠行多少有些因缘的男人。”保宪放松膝盖,向前探出身子。保宪称父亲贺茂忠行为忠行,称平贞盛为男人,这是他一贯的措辞。与晴明称天皇为“那个男人”的情形何其相似。
“听说过。您说的是玄德法师斋戒的事情吧。”
“没错,正是。”保宪拍了下膝盖,便讲述起来。
十七八年前,下京一带住着一位名叫玄德的法师,小有家资。
这位法师连续做同样的梦,死去的父亲出现在梦中。
“当心啊,当心啊。”父亲如此说道。
玄德起初并没有在意,可数日之后又梦见了同样的情形。死去的父亲再次出现,嘴唇紧贴在睡梦中的玄德的右耳,悄悄地说:“当心啊,当心啊。”
这个梦做了四次。玄德终于害怕起来,请阴阳师占卜吉凶。托付的正是贺茂忠行。
“从即日起,七天之内,你一定要坚守物忌①。”忠行如此说道,“否则,会因盗贼之事而亡命。”
于是,玄德立刻折回府邸,开始物忌。
第七天傍晚时分,外面传来叩门声。但不管是什么人来拜访,绝不能开门。玄德不敢出声,躲在府里。本以为不久后对方便会断念而归,岂料这不速之客竟越发使劲地叩起门来。
玄德打发用人从门内问道:“是谁啊?”
“平贞盛。”门外传来回答。
平贞盛可是玄德的故交。但即便是故友,也不能轻易开门。
“我家主人正在坚守物忌。”用人告诉门外的访客,如果有事就在门外说好了。可贞盛竟答道:“今天也是我的归忌日。”
所谓归忌日,其理与物忌是相通的,只是必须要做与物忌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忌讳归来。总之,如果说物忌是禁止外出或开门纳客,这归忌就是禁止归宅了。人在归忌日时,严禁当日回家,必须在别人家住一宿,第二日才能回家。
“但是,我家主人严禁开门。”用人答道。
“如此严格!这究竟是什么物忌?”贞盛问道。用人从门内解释原委:“占卜说会因盗贼之事而亡命,所以要坚守物忌。”
结果,贞盛竟在门后哈哈大笑起来。“那为何要赶我回去?既然是这样,就更应该把我请进来,放我在这府邸中啊。”
用人把贞盛的话传给玄德,玄德觉得有道理,于是亲自到门口与贞盛打招呼。
“请恕刚才失礼。大人所言极是。既然是大人的归忌日,今晚确实不便回家。小僧现在就为您开门,请您务必赏光。”
“哦。”贞盛答道,“那么,只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玄德正在物忌中,你们今夜就先回去,明日再来这里接我。”他把随从都打发了回去。
门开了。只有贞盛一人手持刀弓进来。玄德欲悉心侍奉,却被贞盛谢绝:“既然是物忌之中,也不必费周折了。我就在厢房里凑合一宿吧。”
贞盛对这府邸很熟悉,说罢径自进入了靠近脱鞋处的一间厢房。用完简单的饭食后,熄灯睡下。
到了半夜时分,外面传来细微的声响,贞盛睁开眼睛。
传来推门的声音。此时,贞盛已经腰悬太刀,背负箭筒,手搭劲弓。侧耳一听,许多贼人正纷纷闯进门来。
借着夜色,贞盛潜行至车棚,寻一暗处隐藏起来。
十多人从门口闯了过来。
“这里就是玄德的宅邸。”“听说他攒了不少钱呢。”贼人在黑暗中窃窃私语。
果然是盗贼。盗贼们顺着宅邸的南面摸进去。借着夜色,贞盛也混入其中。一名盗贼点上火把,正欲闯入府内,这时,贞盛忽然喊道:“这里有宝贝,从这里闯进去。”
贞盛故意瞎说,想把盗贼诱到什么东西也没有的地方去。可一旦让盗贼闯进去,玄德法师仍有被杀的可能,于是他故意留在了后面。
前面一名领头的抬脚踹门,正欲闯进。这时,贞盛从背后的箭筒中抽出箭来,搭在弓上,嗖地射了出去。正中那人后心。
“有人在后面放冷箭。”就在对方中箭的一刹那,贞盛大喊起来,接着纵身跳到中箭那人的身后,与他一同倒向屋内。
“快逃啊。”贞盛一面把自己射杀的男人拖进屋内,一面大喊。然而,盗贼们没有畏缩。“别管他,闯进去。”
紧接着,贞盛再次放出一箭,正中这名叫嚣者的脸。
“又有人射箭,快逃啊。”贞盛一面抱住栽倒的男人往屋内拖,一面又大声喊道。
“哇—”于是乎,盗贼们叫嚷着逃走了。
贞盛在背后又连射几箭,又有二人倒下。盗贼们争抢着向门口窜去,贞盛又射杀了二人,射中了第七人的腰。中箭的男人跌倒在路旁的沟中,只有他活到了次日早上,于是将他抓起来,让其供出了同党。逃走的余党悉数被抓。原来这些盗贼都是平将门之乱时将门麾下的武士,将门死后,生活无以为继,于是落草为寇。
“啊呀,多亏把贞盛大人请进来啊。”玄德法师感恩戴德地说。
“如果死守物忌,不让贞盛大人进去的话,法师必被杀害。”
如此,人们便交相传颂起来。
“有这样的事情?”晴明说道。
“忠行的占卜,既不能说中了,也不能说没中啊。”保宪苦笑道。
“不,倘若忠行不让他坚守物忌,贞盛大人当晚定会酣然睡去,自然不会如此警觉。这样一来玄德或许就把命给丢了。”晴明说道。
“言之有理,想想也的确是这么回事。”
“玄德保住性命的关键就在这里。”
“嗯。”
“这件事发生在将门大人死后的第二年—天庆五年前后吧?”
“现在是天德四年,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说起平贞盛大人,是叛乱时与俵藤太大人共战将门大人的那位?”
“对。”
“现在有多大年纪了?”晴明问道。
“大概六十岁吧。”回答的是博雅。
“曾一度被委任为丹波守,去年返回京城,不是吗?”博雅注视着晴明和保宪,说道。
“没错。”保宪点点头。
“最近一段时间可没看见他的影子,听说是患了病?”
“是的。”保宪向博雅点点头。
“你刚才说有事相求,就是这件事吗?”晴明问道。
“嗯。”保宪点点头。他压低声音,悄悄说道,“听说是患了疮。”
“疮?”
“脸上长出一个恶疮,怎么也治不好。”
“治不好?”
“似乎不是一般的疮。”
“什么样的?”
“说是长在旧刀伤处。”
“刀伤?”
“这刀伤似乎大有内情。”
“哦?”
“不知是自然长出的疮,还是被人下了咒。”
“咒?”
“嗯。”
“那么,你打算让我怎么做呢?”
“我想让你给贞盛大人治一下疮。”
“保宪大人你亲自治疗岂不更好?”
“你不知道,晴明。对方其实并不知道此事。”
“不知道?”
“也就是说,是我们这边想为贞盛大人治疮。”
“跟他说一下不就得了?”
“说了,不过不是我说的。是贞盛身边的人说,让阴阳师或药师给看看如何?”
“结果呢?”
“他不听。”
“不听?为何?”
“说是不用管,到时候就会自然痊愈。”
“真的?”
“那谁知道。”
“……”
“拜托了,晴明!”保宪一副哀求的表情,说道,“去一个并不希望别人医治的人身边,硬给他治疗,这可不是我的拿手戏啊。”
“既然如此,那就依他本人的意愿,不去管它不就行了?”
“那也不行。”
“为何?”
“……”
“为何不行?”
“事实上,关于这个疮,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
“说实话,我不能讲。”
“那就不好办了。”
“别啊,晴明。否则我就麻烦了。”
“保宪大人你也会有麻烦?”
“啊。”保宪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要是我事先透露点什么给你,你就会动摇的。”
“……”
“如果你愿意,那就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二人来个殊途同归。”
“为贞盛大人治疮吗?”
“是。”
晴明盯着保宪,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恐怕不是你一人的想法吧。”
“嗯。”
“保宪大人,你身后一定还有人物吧?”
“嗯。”
“谁?”
“不能说。”
“是那个男人?”
保宪没有作答。“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晴明。”他微笑道,“不久就是宫内歌会了。在歌会结束之前,你就不要动了。”
“歌会结束之后呢?”
“你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到贞盛那里露个面,说句‘听说您患病了,如不嫌弃就让我给您看看’之类的就行。”
“我可不敢打包票。”
“别这样。你最合适了, 晴明。”保宪使劲拍了下晴明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