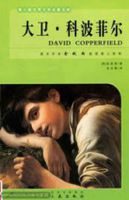第二十九章
埃德娜甚至等不及丈夫的回信,听他对这件事的意见,自己已经加快准备工作的步伐,从埃斯普兰德街的家里搬到本街区拐角处的小房子去。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表现在她的每个行动之中,一经想到,便立刻实现,中间毫不犹豫,从不等待。第二天一大早,埃德娜在阿罗宾的社会圈子里度过几小时之后,便匆匆赶往新居,忙于布置。但她一回到原来的大房子,便觉得有如踏进了禁止入内的某个寺庙,千百个声音在命令她出去。
在大房子里,凡是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即不是丈夫施舍给她的一切东西,埃德娜全都叫人搬到小房子去,靠自己的经济来源,维持简单拮据的生活。
阿罗宾下午来到小房子外面,朝内窥视,发现埃德娜高高地卷起袖子,正同女仆一道忙碌。她精神百倍,身体健壮,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漂亮过。她身着蓝色的旧袍,头上胡乱地结着一块红丝手帕,以保护头发不沾灰尘。他进门的时候,她正站在高梯子上,从墙上取一幅画。他早已发现前门大开,就从窗子那边转过来,毫不拘束地进了屋子。
“下来!”他说。“你不要命了?”她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招呼他,显得正沉浸于忙自己的活儿。
要是阿罗宾曾盼望见到她含情脉脉、一副娇嗔之态,或哭哭啼啼的哀痛之状的话,他肯定已经大吃一惊。
毫无疑问,做好了一切应急的准备,以防患于未然,好像他正一心致力于即将发生的事。“请下来吧。”他坚持道,手扶梯子,两眼望着她。
“不,”她回答说,“埃伦害怕登梯子,乔又在‘鸽子笼’那边忙乎——这个名字是埃伦取的,因为那房间太小,看起来有如鸽子笼——可总得有人登梯子呀。”
阿罗宾脱掉外衣,表示自己乐意,也心甘情愿替她冒险。埃伦给他拿来一顶自己的防尘帽,当她看见阿罗宾在镜前戴上帽子的古怪相时,再也忍不住了,笑得死去活来。埃德娜应他之求为他系上帽带时,也忍不住笑出声来。因此,现在他爬上梯子,取下那些画和窗帘,由埃德娜指点着拆下那些装饰品。他干完之后,便摘下防尘帽,到室外去洗手。
当他再次进屋时,埃德娜坐在小凳上,无所事事地梳理着地毯上那把掸子的羽毛。
“还有另外的事要我干吗?”他问道。
“全完了,”她答道,“其余的事,埃伦可以对付。”她把年轻女仆留在客厅里,不愿意单独同阿罗宾留在那儿。
“晚宴怎么样啦?”他问道,“那件大事——一场政变?”
“后天举行。为什么你把它称之为‘一场政变’呢?嘿!那好极了,一切都是最上等的——水晶玻璃制品、金银器皿、精工陶瓷、鲜花、音乐,还有任其自便的香槟。我要让莱昂斯付账。我不知道他一见账单会说些什么呢?”
“你刚才不是问我为什么要称之为一场政变吗?”阿罗宾已经穿好外衣,站在她的面前说道,并问他的领带是否垂直。她对他说已经垂直了,一点儿也不比他的领夹高。
“你什么时候搬进‘鸽子笼’呢?——这全得感谢埃伦呵。”
“后天,晚宴完了以后,我要在这儿睡觉。”
“埃伦,你能不能发发善心,给我一杯水呢?”阿罗宾问道,“要是你原谅我提起这件事的话,窗帘上的灰尘已经呛得我的喉头干焦了。”
“埃伦去拿水的时候,”埃德娜说着站了起来,“我也得说再见,让你离开啦。我必须去把这些污垢清除掉,还有上百件的事需要做,需要想呵。”
“我什么时候来看你呢?”阿罗宾问道,竭力想把她留下,因为女仆已离开了房间。
“当然是在晚宴之时嘛。我也要请你哩。”
“不能在这之前吗?不能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上午,或者明天中午或晚上吗?或者后天上午或中午吗?难道我不告诉你,你就看不出来吗?你要我等到何年何月啊?”
他已经跟进了大厅,来到楼梯脚。她正上楼,半转过头来对着他。他抬起头,仰望着她。
“一点儿也不能早。”她说着大笑起来,眼睛盯住他。这立刻给了他等待的勇气,也成为等待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