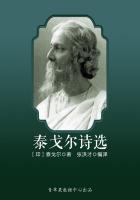显然,这种主导性的叙事元素规约了新文学创作思想的走向,那种无视人的存在意义的创作、那种游戏人生的创作,以及那种所谓田园牧歌情调的创作,都将受到质疑,受到批评。茅盾说,新文学必须“是站在反封建的自觉上去攻击封建制度的形象的作物——旧文艺”,并着重强调:“这是‘五四’文学运动初期的一个主要的特性,也是一条正确的路径。”同时,“为人生文学”的创作观念还强调新文学的表现对象,必须是民族大多数的普通人(包括知识分子)与他们平凡的社会人生,而不是“古之小说”占主角的“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而在“‘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的成型,将有效地规范新文学创作意识的思想性走向,确保新文学对思想文化启蒙历史重任的承担和艺术表现。
作为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鲁迅一开始就在他的创作中显示出了他那种“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他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且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最为深刻、最为形象的认识结论。通过文学创作,鲁迅把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从中展现出中国人的生存境况、心理性格和历史命运,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鲁迅给自己的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花”,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显然,鲁迅的意识聚焦,不是有关贫苦国民在物质层面——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占国民大多数的、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下层贫苦国民,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与心理变异。
在小说《祝福》里,鲁迅并没有写鲁四老爷如何在经济上剥削祥林嫂,也没有正面描写祥林嫂在物质上的拮据,通篇则是展示以祥林嫂为代表的下层贫苦国民的精神愚昧和麻木。在《故乡》里,鲁迅描绘的也不是他那久别的故乡的“阳光灿烂”,不是他回到故乡的那种“欢欣鼓舞”,而是闰土那“老爷”声中透露出来的精神隔膜。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他的《阿Q正传》了。通过对阿Q矛盾性格的揭示,鲁迅把他对国民性——尤其是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思考,推到了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层面,将一个“现代的国民魂灵”展现得活灵活现,将“国民的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悲剧和喜剧紧紧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艺术情感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个体。可以说,居于鲁迅文学创作观念中心的,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及其对人们的影响,而是展现身为国民的“人”,如何获得精神的解放、心灵的解放,如何摆脱长期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而进入精神自由、心灵自由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文学创作集中地体现了他作为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通过文学而展示出来的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心理发展和前途命运,寻找人的精神归宿,建构人的精神家园的思想激情和精神风采。
有人认为鲁迅的创作有思想大于形象之嫌,其实这完全忽视了鲁迅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理念。在他的作品中,他的那种对现实人生所特有的生命感悟,特别是对人生苦楚所怀有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使他对现实人生、社会历史的体察,在达到空前的思想高度的同时,也总是深沉地流露出只有先驱者才可能有的那种时代的忧患意识、那种超前行进中的心理孤独感。这才是鲁迅文学创作的真正特色。他不是那种用什么文艺理论的概念或术语就可以盖棺定论的作家,而是一个真正展现自己生命本质和思想风采的作家。在鲁迅那里,他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源或人的本质之类的抽象问题,而是诸如人生是否有意义、人怎样或应该怎样有意义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更能展现鲁迅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理想。
所以,阅读鲁迅的文学文本,得到的不是思维的快乐和逻辑的满足,而是心灵的颤动和人生的启示。所记住的不是有关人生抽象的大道理,而是能够不时地感受到他那种彻底超越了生与死的纠缠而透露出来的人生睿智、那种“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的人生启示,以及像西西弗斯那样,明明知道将巨石推到山顶便又会滚回原地,但仍然要永不停息地劳作,推着巨石向上艰难行走的人生意志。看,那明明知道前面是“坟”,仍然放不下,仍要向前走的过客,不也是在说:“我还是走的好!”(《过客》)“走”,乃是生命的本质所在,人生的终极所系。所以,海德格尔说:“思最恒久之物是道路。”尽管“至多不过是一条田间小路”,但思则可以“穿过田野,它决不轻言放弃”。不停地走在恒久的道路上,那么,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就尽显其中——真正的人生之“道”也尽显其中。因此,在鲁迅的文学创作当中,思想与形象是紧紧糅合在一起的,对现实人生的本质反映与主体对人生本质、存在意义的思考及其艺术表现也是紧紧糅合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代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这应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鲁迅的创作,深刻地影响了新文学的众多作家的创作,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展现了与鲁迅创作相仿的特点。五四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是“社会问题”小说。以冰心、庐隐、王统照、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叶绍钧、俞平伯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是将小说当作“社会改革的器械”,展现出了新文学对社会人生的强烈关注,以及文学参与社会人生实践的积极主动性。同时,这种创作观念还决定了“社会问题”小说创作的整体兴起,使新文学作家更加注重从身外广大社会的现实人生实践层面上,寻找创作题材,寻找当时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从而使新文学一开始就能够与社会人生实践紧密结合,获得现实主义的创作灵感,对应人们渴望社会变革的心理,体现新文学的理性精神。
(二)对新文学创作大众化走向的有效规约
新文学为新文化承担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在对应时代需要的同时,也还必须对应创作接受对象的需求。在这方面,“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的成型,将有效地规范新文学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的走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新文学的形式提出现代性与通俗性并重的规范,要求巨大的思想性能够以通俗性的表现形式显示出来;二是推动新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使新文学创作在艺术方法上,能够具有更大的选择权利。
陈独秀在倡导文学革命时,曾明确指出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旨在要求新文学创作能够面向大众,让普普通通的大众都能够读懂新文学,接受新文学。当然,新文学要求创作的大众化、通俗化,并不是要降低要求、降低艺术水准,以迎合一些人的低俗要求。相反,新文学一是要求将普通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唤醒他们的主体意识。在这方面,“两浙”作家的创作观念和实践是极其卓越的。如鲁迅,就是出于“改造国民性”的强烈愿望,以沉重苦楚的思想情感,描绘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努力揭示出千百年来普通人过着死水一潭的世俗生活的悲剧,对应他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唤醒他们的思想觉悟。二是充分考虑到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准和阅读习惯,使新文学创作能够向大众提供清晰的、对应大众需求的审美图式和人生图景,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发挥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作用。
如周作人,在倡导“平民文学”时就指出:“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一,平民文学应该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他还着重强调了两点:“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地一个地位……第二,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文学。”强调文学创作的“真诚”,反映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事实”,展现真正的“人”的生活,提升大众的思想文化境界,这对于新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有着明确目的的大众化走向的规约。它使新文学在发展之初,就能够将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文学的通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创作实践上取得了实绩,同时也在批判标榜通俗化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当中取得了胜利。尽管鸳鸯蝴蝶派标榜自己是最通俗的文学,在创作上往往杜撰一个红颜薄命,才子见怜或才子落难,佳人打救之类的凄婉故事,写得悲悲切切、粘粘糊糊,乍眼一看似乎也有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弱者的同情,但实际上则是空虚庸俗的陈词滥调。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就对其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作了全面的清算和批判,将新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与它们划清界限,让大众对此有所区分。
“两浙”作家对“为人生文学”叙事性范式成型的推动,也促使了新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发展。因为创作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涉及新文学如何将思想文化启蒙重任落实到对应广大的民众需求,促使他们觉醒,走向主体高度自觉等相关问题。在五四时期,开放的社会环境,使得外来思潮不断涌入,近代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再加上新文学作家大多在国外留过学,对西方文学创作比较了解,这就使他们在进行新文学创作时,既能够按照自己的创作爱好,又可以对应大众需求的方式来决定创作方法的选择,从而形成了五四新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局面。近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几种主要的创作方法,都为新文学所吸收和采用。
正如钱理群等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时期,并不存在现实主义独尊的现象,现实主义与其他思潮、方法多元并存,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创作局面。”在这方面,“两浙”作家的贡献十分突出,像鲁迅的小说创作,就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如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显示出了“格式的特别”的特点。沈雁冰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这里所说的“新形式”,除了指文学形式结构之新外,应当还包括运用多种创作方法创造“新形式”的涵义。如《狂人日记》,鲁迅一方面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要求来塑造典型人物,展现了受迫害但获得觉醒的“狂人”的形象,他的一举一动都符合狂人(妄想症病人)的特征;但另一方面,鲁迅展现出狂人的每一个真实细节的背后,又给人以一种象征性的深刻寓意,具有象征主义的艺术表现特征。可以说,多样性创作方法的广泛运用,给予了新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为新文学的艺术表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之能够更好地对应大众的需要,进而推动新文学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