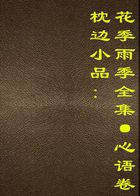一、绪 论
明代文学尤其是中晚明文学,是体现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重要一环,从文学思想到文学体制,均有许多新变因素发生。这种种新变因素,与之后日渐突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实现近现代转型的进程中,构成怎样的关系?解答这一问题的意义,恐怕并不限于中国文学本身。而在整个东亚社会范围内,自这一时代起,如何通过交流、传播机制,在文学近代化的道路上形成某种共趋的演进态势和各自特点,更是中韩日学界普遍所关心的。本文即拟通过有关许筠与朝、明文学交流的再检讨,就上述问题作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有关明代文学与同期日本一侧的交流情况,笔者在十年前曾有专文予以粗略地探讨,这里就不再阑入。
许筠(1569—1618),字端甫,号蛟山、惺叟、惺惺居士、鹤山、白月居士等,阳川人。宣祖二十七年(1594)廷试乙科及第,历任艺文阁检阅兼春秋纪事官、世子侍讲院说书,兵曹佐郎,黄海都事,成均馆司艺,遂安郡守,三陟府使,公州牧使,刑曹、礼曹、户曹参议,承文院副提调,左副承旨,刑曹判书,左参赞等职,光海君十年(1618)坐谋逆处死。著有《惺所覆瓿稿》
二十六卷(包括《惺叟诗话》一卷)、《蛟山臆记诗》二卷、《闲情录》十七卷、《鹤山樵谈》一卷、《国朝诗删》九卷及谚文小说《洪吉童传》等。
作为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又是先后以陈奏使、千秋使、陈奏副使访明并三次担任远接使从事官的外交家,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得他在朝、明文学交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他所处身的时代,就明朝来说,恰是包括文学思想与创作在内的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纷然剧变的万历中后期;就朝鲜朝来说,亦是文学及思想文化开始发生转变的一大关捩。探讨他在这一时期所担当的文学、文化交流作用,意义尤为重大。有关许筠研究,韩国与中国学术界均已有丰硕的成果,笔者则不揣简陋,试图在整个东亚文学由中世向近代过渡的视阈下,从与许筠相关的具体文学事象入手,对其于双方文学交流的贡献及意义重新予以体认。
二、许筠与《朝鲜诗选》
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文化、文学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韩民族的文学艺术也很早就通过种种途径有所传来,但直至晚明,才开始出现中国人自己搜辑、编纂朝鲜诗歌选集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契机,即是所谓的“壬辰之乱”,一方面因此一事件增强了明代朝野对朝鲜的关注度,一方面令一些随援军入朝的士人有实地接触、交流的机会,吴明济编纂的《朝鲜诗选》便是此际相当重要的一部。
长期以来,中韩学术界皆以为此编已佚,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教授于1998 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此编朝鲜刊本,并于次年以《朝鲜诗选校注》(辽宁民族出版社)整理出版,终令完璧重见天日。此本共七卷,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分卷编次,没有目录、小传,卷首有韩初命序、吴明济自序,卷末有许筠《朝鲜诗选后序》。韩序为朝鲜梁庆遇(1568—1642 前后)书,末署“明万历庚子(1600)仲春下浣东乾隆《绍兴府志·经籍志》著录其《朝鲜世纪》一卷。
莱韩初命撰”,吴序末署“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己亥夏四月壬午之望玄圃山人吴明济书于朝鲜王京李氏议政堂”,许序末署“皇明万历廿八年庚子季春上浣朝鲜许筠顿首再拜书”,知此编当于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朝鲜宣祖三十二年)在朝鲜纂成,并于次年春梓行。其正文卷七末页尚有一行黑色印戳———“朝鲜状元许筠书”,可知系据许氏手书刊刻。
尽管如此,有关此编的版本、卷数仍有一些疑问存在。致力于此集研究的韩国顺天乡大学校朴现圭教授与上述祁庆富教授,都曾注意到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也是园书目》、朱彝尊《明诗综采摭书目》于此编皆有著录,然实际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总集类”即已著录:“吴明济《朝鲜诗选》八卷(一作四卷。明济,一作济,字子鱼,会稽人)。”首先,上述朝鲜刊本明明只有七卷,何以《千顷堂书目》著录为八卷?是另有一种八卷本或明刊八卷本,还是此版朝鲜刊本后印时增补了卷首目录一卷?因为据朝鲜尹国馨撰《甲辰漫录》,他于壬寅(1602)仲夏后自家乡黄岗还京城,所见新印吴明济纂《朝鲜诗选》:
所谓诗选者非但选诗而已。其卷首目录,书我东历代易姓始末。崔致远以下,至于今日,宰枢、朝士、闺秀、僧家百余人,列书姓名,且疏出处等事。此非得于道听,必是文人解事者之所指授,第未知的出谁手也。余之名下,曰官至刑曹参判,今归老汉江,而末端壬寅春正月吉日续补云云。
于所谓的卷首目录,从收录家数至列书姓名、出处的著录方式,交代得非常清楚,且有关于自己小传的细节,如此具体,恐很难以“不符合实际”轻易予以否定。其次,《千顷堂书目》著录“一作四卷”,是否即意味着另有一四卷本的版本?乃刊于朝鲜后又在国内另梓?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此编时,未注明卷数,而钱曾、朱彝尊之书目著录此编时,皆作“四卷”。是否在清代更流行四卷本?此四卷本与八卷本或七卷本关系如何?虽然笔者已查知,(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未刊稿本中原收有吴明济《朝鲜诗选》四卷,然在进一步搜核这方面资料前,这些问题都还不能得到解决。
关于《朝鲜诗选》编刊之缘起及经过,诸序皆有交代,而以吴氏自序最为详具。据是序,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编者吴明济以幕僚身份,从徐司马公赞画东援朝鲜,其入朝实在次年季春。先是,军于义州,与朝鲜李文学赋诗相赠,李氏复引见其他文学之士,今选集中所录“李秀才”、“蓝秀才”诗各一首,当即此际所赋赠。于是,吴氏遂求访海东诸名士集,诸文学以丧乱无存相告,唯以记忆得一二百篇。及抵汉城,馆于许筠兄弟家,许筠“能诵东诗数百篇,于是济所积日富;复得其妹氏诗二百篇”。
此间又得尹根寿(1537—1616)及诸文学多搜残编,规模大体始具。不久,徐司马公以外艰归乡,吴氏亦还京师,以所得东诗及许景樊诗示诸缙绅,博得好评。万历己亥(1599)(此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吴氏重赴朝鲜,馆于议政李德馨(1561—1613),益请搜诸名人集。于是,前后所得,自新罗及今朝鲜,共百余家。于两月中披览拣选,是年四月初成此编。由是观之,此编材料来源之主体部分由许筠提供,当无疑问,李秀才等最初提供了一部分,未必不为许氏所覆盖,尹根寿、李德馨等的作用,则以搜残补遗为主。而据许筠手书此编付梓,又为撰后序,亦可见其自身重视的程度。许氏与吴明济之间的交谊,由《诗选》所录其酬赠吴氏诸诗可窥一斑。
虽然此编所得,绝大多数率皆据记诵载录,如吴氏自序所谓“而所得率烬余,其全帙不二三家,或不能无遗珠之叹”,因而在资料的准确性方面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诸如误记、字句变更与遗漏等,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因为由许筠这样深谙本国文学历史与现状的著名文学家提供助力,仍使该编具有相当高的价值。我们知道,许氏于二十五岁完成了当代诗论著作《鹤山樵谈》,上起金宗直(1431—1492),下迄李德馨,距其向吴明济提供东诗资料不过四年时间,故以其博闻强记,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朝鲜诗人作品的准确性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上引尹国馨《甲辰漫录》,据卷首目录所书之详,以为“此非得于道听,必是文人解事者之所指授”,亦可佐证。不仅如此,许氏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在他提供东诗材料的同时,无论从收录范围到选诗标准,皆应首先烙上其个人的印记。尽管如梁命津《(梁庆遇)家状》,谓“皇明学士吴明济,东来采诗,自新罗暨本朝名公,其简甚严”,但吴氏之拣选,须在许氏所提供的“底本”之基础上方可得以进行,则其作为朝鲜人,并且是富于识见的朝鲜文学批评家所提供的视角,不仅使得这部诗选具有某种权威性,而且体现了交流的双向互动性。故在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应是将许氏《鹤山樵谈》乃至具有诗史性质的《惺叟诗话》、当代诗选《国朝诗删》等著作,与吴氏《朝鲜诗选》作更为深细的比对,梳理双方文本的内在联系与差异。惜本文限于时间与资料条件,尚无法展开这样的工作。
吴明济《朝鲜诗选》在中国国内的影响,至少随着像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这样的经典诗歌总集传播开去,这也意味着许筠所耗费的心血有所结果。钱谦益在《列朝诗集》闰集《朝鲜》卷首几乎全文载录了吴氏此编自序并摘录许氏后序,以表明其资料来源。有学者已作统计,《列朝诗集》所收作者与《朝鲜诗选》同者33人,选诗169首,同者93首。其中所选诗均为《诗选》所收者20 人,诗40 首。《诗集》有而《诗选》未收者仅25首;二编所选诗人同而诗全然不同者,仅2人3 首。可见钱氏此集确以吴氏《朝鲜诗选》为主要依据。而据朱彝尊自述:
自元以前,诗曾经大司成鸡林崔瀣彦明父选录,目曰《东人之文》,凡二十五卷,度必有可观,惜无从访求。今之存者,仅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愚山为王氏诸臣白冤,可谓发潜德幽光矣。予更证以《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史略》、《殊域周咨录》、《皇华集》、《輶轩录》,订其异同,补其疏漏,论次稍加详焉。
崔瀣(1287—1340),字彦明,号寿翁、拙翁,《高丽史》卷一百九有传。其所选本国名贤诗文之集———《东人之文》二十五卷,为今可考知最早的一种诗文选本,全书已佚。而晚明中国人编纂的《朝鲜诗选》,原有焦竑、吴明济、蓝芳威等数种,清初又有孙致弥《朝鲜采风录》。朱彝尊谓其时仅存吴氏此编固然不确,然亦可见唯吴编稍见流行,故仍以为主要依据,而以相关诸籍予以订补。上举学者亦曾有统计,谓《明诗综》录朝鲜诗人90 家,137首,虽选取范围更广,然与吴氏《朝鲜诗选》同者仍有27人,其中20人的24首全然出自该选。
以“壬辰之乱”为契机,这个时代终于出现了由中国文人编纂的朝鲜诗歌选集,并对此后的清代亦产生影响,这可以说是双方文学交流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由吴明济这样未获得更高级功名者来担当朝鲜一地诗歌创作的搜辑、编纂工作,本身就体现了某种近世文学的特征。不过,我们也应看到,虽然这种交流已具双向互动的性质,然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其信息交换仍不对称。从传播方来说,其介绍朝鲜文学,主要是与汉文学中心部趋同的“华诗”一侧,体现的仍是中世普遍主义“汉文学扩散”
的特征,故如许筠于其《后序》,有“昔周官采诗,三韩不与;夫子删诗,三韩不及,远莫致乎!夫遗乎千载前,而遇于千载后,小国之音,以先生始与成周齿,岂非天耶”之表述;而从接受方来说,除了采风以备一方文献外,又有较为明显的述异猎奇之成分,这从许氏提供的其姊妹许景樊诗在晚明士人阶层中流传最广的事例可以看到。
许景樊(1563—1589),本名楚姬,景樊其字,号兰雪轩。
其诗最早传入中国,即由吴明济从许筠处获得,有二百篇之多,而据《朝鲜诗选》朝鲜刊本所录许景樊《游仙曲》题下吴氏自注:
“凡三百首,余得其手书八十一首。”吴氏万历二十六年(1598)按:据其年,当为许筠之姐。许筠《上西厓相》:“辛卯岁,辱制亡姊诗序文以惠。”(《惺所覆瓿稿》卷二○,抄本,《韩国文集丛刊》第74册)《千顷堂书目》、《列朝诗集小传》等所记有误。
归国,其《游仙曲》诸篇,已为都中人士注目。此后,万历三十四年(1606),明皇长孙诞生,诏遣翰林修撰朱之蕃、刑科都给事中梁有年至朝鲜,时由许筠担任远接使从事官,朱氏得兰雪之集,梁有年为序而传之,一时朝野遂至轰动。当时朝中士大夫如谢杰(约1545—1605)有《朝鲜许状元妹次孙内翰诗殊佳丽因步其韵赏之》,郭子章(1542—1618)则录有《朝鲜许兰雪曲》;著名文人潘之恒(1556—1622),在为范允临妻徐媛、赵宧光妻陆卿子诗集作序时,亦以许兰雪相比曰:“许景樊,夷女,尚擅誉朝鲜,夸于华夏,而况我明文章辞翰,炳耀于前者乎?”至如闺秀士妇,更是口吟手摹,如嘉兴项鼎铉在其《呼桓日记》中,即记其妻沈无非“有手书所撰朝鲜许士女集小序一首”,并谓“是编为箕国士女许景樊诗若文,秀色逼人,咄咄无胭粉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许景樊传中则录柳如是所评语曰:“许妹氏诗,散华落藻,脍炙人口。”然亦一一指出其诗多沿袭唐人旧句处,并本朝马浩澜《游仙词》,亦窜入其中,以为“岂中华篇什,流传鸡林,彼中以为琅函秘册,非人世所经见,遂欲掩而有之耶?此邦文士,搜奇猎异,徒见出于外夷女子,惊喜赞叹,不复核其从来。”还指责方维仪采辑诗史,评徐媛诗以“好名无学”遍诮吴中士女,而于许妹之诗,则漫无简括,可见柳氏胸中,亦有一许景樊以为对手,虽不免有苛求处,然其所读所校,亦可谓深细焉。其实作诗化用前人旧句,本来就是学诗者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倒或可自其袭用之所从来,窥见其诗学之宗尚。
三、许筠与明代中后期文学
有关许筠在明代文学接受与传播中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已日渐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不过,以笔者相当有限之所见,已有研究中对于许氏接受明代文学的考察,或偏于前后七子复古风尚的影响,或偏于“性情”说诗学观念的转换,或偏于小说及其批评的引介,似尚未能就中晚明文学新变思潮的整体演进脉络,得出一整合的图景。此外,对于其发挥作用的文化史背景及其意义,似亦仍有可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鉴于当时大的政治格局以及朝鲜特定的锁国社会条件,有关许筠在明代文学接受与传播中的作用,仍须纳入朝贡制度下的“赴京行使”这一几乎是唯一的文化通道之历史变迁及其意义予以探讨。简单说来,朝鲜朝建立之初,为实行儒家王道的需要,中国典籍的输入已经开始,然其时的输入方式只是“赐书”一端,那意味着更多地具有政治或外交上的意义。世宗朝以更为积极的文化政策,通过“赴京行使”,发展起相当活跃的“贸书”活动,尽管其输入仍以经史为主,却使得一种文化受容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其后的朝代在此项政策上因趋于保守而曾一度中止,然至中宗朝重又恢复,并已充分认识到输入与刊行中国典籍的文化意义,这可以说为许筠所处的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许筠一生曾数度出使明朝,每次都可谓“图书满箧行装富”。如其《闲情录· 凡例》曾记1614 年、1615 年(万历四十二、四十三年,光海君七、八年)再使明朝曰:“甲寅、乙卯两年,因事再赴帝都,斥家赀购得书籍凡四千余卷。”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致力于文学事业的作家、学者,根据他本人文集中所提到的阅读范围,我们尚可以窥见他在大量输入中国典籍中对于明代文学的侧重,其种类从明人别集、总集到笔记、杂传、小说等,一应俱全。而其每次担任远接使从事官,也总是迫不及待地向明使打探当今文坛的消息,如1606 年接待朱之蕃、梁有年:“余因问曾见弇州否,上使曰:癸巳春,往太仓,请益于弇州。公时以南大司寇致仕…… 余问方今翰阁能诗者孰谁?曰:南师仲、区大相、顾起元俱善矣。有兵部郎谢肇淛,诗酷造大复之域也。”1609年接待明册封诏使太监刘实,有监生徐明等随从:“余又问文章孰为第一。徐曰:自太仓、新安之仙去,海内部署文章者无人焉,屠赤水隆、黄葵阳洪宪有盛名于东南。此外,谢郎中肇淛、区洗马大相、顾编修起元为后来之秀。”这其实是富有意义的。
文学虽然向来被视作是经国之大业,但实际上却始终具有个人修养与审美趣味的含义,尤其当时代进入近世,明代文学尤其是中晚明文学,可以说是蕴涵着社会文化思潮变革种种征象的富矿,作为官方的外交人员,能够从个体的趣尚出发输入相关信息,则其所具有的相对广泛的文化交流意义更为显著。
那么,许氏在万历朝后期所接受、传播的,主要是明代文坛的哪些信息呢?在整个东亚社会尚未被近代西方文明突入之前,有一种关于文化传播的看法,不说其流行,亦显得不约而同,那就是从汉文学圈的中心部到周边地区,文学风尚的传递存在着一种“时间差”。如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汉文学家江村北海(1713—1788),在其《日本诗史》卷四中即谓:“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
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无独有偶,李德懋(1741—1793)亦曾指出:“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始厌也。”确实,因为地理上的距离与当时交通条件的关系,这样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化传播的因素相当复杂,更为关键的可能是双方社会自身的文化条件及受容方在迎拒之间的内应力,故其说其实还是相当笼统或表象的。然或许是此类看法的潜在影响,文学史研究中的传统观点,一般皆将宣祖朝以包括许筠所师事的李达在内的“三唐诗人”,终结国初以来盛极一时的苏、黄诗风,开启学唐之风,视作是明前后七子一派复古风尚影响的结果。如金台俊即将之归结为“明朝万历文化东传发挥了间接作用”,赵钟业在其《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中亦指出:
及于宣祖朝,则遂至于批评宋诗,渐变为倾向唐诗。此亦因于明代复古之风,尊唐黜宋之说,而亦影响于韩国故也。
而许筠所持之诗论,主要亦被定位在此“尊唐黜宋”之上。从大方向上来说,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准确并有据的,即便在中国文坛,前后七子一派的势力,亦有相当持久的影响,钱谦益甚至说:
“循声赞诵者,迄今百年,尚未衰止。”而从许筠集中,诸如《读崆峒集》、《读大复集》、《读徐迪功集》、《读沧溟集》、《读弇州四部稿》、《读边华泉集》、《读谢山人集》、《读王奉常集》、《读徐天目、吴甔甀集》等对前后七子的精研,其《惺所覆瓿稿》仿王世贞四部稿之例,《国朝诗删》仿李攀龙《古今诗删》之体,也确可窥见前后七子一派对于他的重大影响。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至万历中后期文坛,面对前后七子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话语权力,人们早已纷然思求其变,如当时永嘉何白曾概述说:
于是词家徒知厌薄剽剥辈,又漫不知宗旨所在,乃各立坛坫,务标一帜。或持一说者,以谓古选必斤斤步趋汉魏,近体必字字临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不力,所就非不宛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颇为拟议所拘,又且不敢熟读李、杜、高、岑、韩、柳、元、白诸家,以穷其变。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剪彩琢叶手耳,虽雕绘满眼,殊少气韵生动之趣。或持一说者,以为诗为心声,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无尽,吾诗亦无尽。当其目之所触,牛溲马通,无非上药,外无乏境,内无乏思。此论未尝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杂,则有秽冗之讥;矢口成篇,复伤率易之病。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丛谈小说部耳。虽胸次如洗,殊少淘汰谨严之法。又持一说者,立意以枯淡玄远为宗,清癯骨立,宁为生硬,而不为圆熟;宁为冲夷,不为浓艳。残山剩水,非不清绝,正如赵令穰画情境,不越百里。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声闻小乘耳,虽洗涤雅洁,殊少博大浩瀚之观。呜呼!其中矮人观场者,或各为楚汉左右袒,且信且疑,终无成立,此道不复归一,无论古法,即何李宗派亦不可续矣。
这里所举述的三种最具标志性的主张,毫无疑问,分别以调和、改造的复古派后劲及激烈反对的公安与竟陵为代表,它们构成了整个万历中后期文坛纷争消长之多极格局的基础。尽管论者对此三大流派的持说及创作作出了不甚满意的评价,但从其描述当中,我们却正好可以了解到嘉、隆之际至万历中后期文坛风气嬗变的过程全貌,而从当时人们“纷然自为跳逸”的思变心态及所作的种种努力,我们也可看到晚明文学实现新变的基础及其必然性。
因此,鉴于许筠所处的时代及他与明朝交流之直捷,所获得的应该是这一时期文坛剧变一种即时的、全息的信息。他所编选的中国诗选本,如《古诗选》、《唐诗选》、《四体盛唐诗》、《唐诗选删》、《宋五家诗抄》、《明诗删》、《明四家诗选》等,看上去似乎体现了李攀龙《古今诗删》弃宋元而绍述唐以上,于本朝则与王世贞接续北地、信阳而独尊的宗旨,其实恰恰反映了万历中期以来当时文坛于七子复古学说在迎拒之间,而古、唐诗歌选本等大为流行的一种影响,因为针对李攀龙《古今诗删》的巨大影响力,其时坊间不仅有题李攀龙编、唐汝询注、蒋一葵直解的《唐诗选》
七卷,题李攀龙编选、钱谦益评注的万历庚戌(1610)刊本《唐诗选玉》七卷,题李攀龙选、袁宏道校的万历戊午(1618)居仁堂刊本《唐诗训解》七卷乃至王稚登批点本等仿袭、射利之作涌现,文人亦乘其波流,而有诸如张之象编纂《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吴绾准冯惟讷《古诗纪》增辑《唐诗纪》,唐汝谔、唐汝询兄弟分别编纂《古诗解》、《唐诗解》,臧懋循编纂《诗所》、《唐诗所》,乃至锺惺、谭元春编纂《古诗归》、《唐诗归》等众多诗歌选本相角力。考察许筠所体现的诗学方面的认识,固然有诸多与前后七子如出一辙之处,如其于《国朝诗删》的自负,谓“以余之薄识浅见,会众说而去就之,宜删其之劳也。虽然有不合而弃之,沧海或叹其遗珠也。
至于不合度而进之者,则无有焉,庶免鱼目相昆(混)之诮也”,与王世贞评说李攀龙《诗删》所谓“今于鳞以意而轻退古之作者间有之,于鳞舍格而轻进古之作者则无是也。以于鳞之毋轻进,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楷模后之操觚者,亦庶几可矣”,可谓同一声口,模拟之迹显而易见;至如他在《宋五家诗钞序》所表述的观点:
诗至于宋,可谓亡矣。所谓亡者,非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诗之理不在于详尽婉曲,而在于辞绝意续,旨近趣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为最上乘,而唐人之诗,往往近之矣。宋代作者不为不少,俱好尽意而务引事,且以险韵窘押,自伤其格,殊不知千篇万首都是牌坊臭腐语,其去诗道数万由旬,岂不可悲也夫。
又显然承李梦阳所论而来,李氏在《缶音序》中即谓:“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夫诗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者也。难言不测之妙,感触突发,流动情思,故其气柔厚,其声悠扬,其言切而不迫……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诗何尝无理,若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邪?”但是,试观许筠《明四家诗选序》论明诗:
明人作诗者,辄曰吾盛唐也,吾李杜也,吾六朝也,吾汉魏也,自相标榜,皆以为可主文盟。以余观之,或剽其语,或袭其意,俱不免屋下架屋,而夸以自大,其不几于夜郎王耶?
《鹤山樵谈》论明文:
明人以文鸣者十大家……而崆峒专学西汉,王、李则钩章棘句,欲轶先秦,南溟华健,董、茅则平熟,王慎中则富赡……王元美辈以明人文章比西汉,以献吉比太史公,于鳞则子云,自托于相如,其自夸太甚。
于七子一派及其流风所及,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应该是站在了万历中后期各派文人普遍地对七子拟古之弊有比较深刻的反省立场之上。尽管竟陵派的影响要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秋冬刊行《诗归》以后方显,对于许氏来说,或尚不及关注,然从其《闲情录·凡例》中提到“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不熟此传者保面饔肠,非饮徒也”,引用的是袁宏道《觞政》中的句子,至少其于1614年、1615 年赴明之际已购得中郎文集是很可能的事;又朴现圭教授新近有专文探讨许氏如何求得李贽著作,皆可证实其于此间新的文学思潮与趣尚已有所接触(在其集中,即有《读李氏〈焚书〉》、《题袁中郎〈酒评〉后》等作)。故不仅其为人熟悉的所谓“吾则惧其似唐似宋,而欲人曰:许子之诗也”,明显如晚明性灵诗人之声口;从“许筠倡言曰:男女情欲,天;分别伦纪,圣人之教也。宁违于圣人,不敢违天禀之本性也”,亦可见有类似童心说的思想存在,这在其《诗辨》、《文说》
等有关文学的论述中有更多的体现。他在诗歌表现性情方面的主张,当然可以追溯至李梦阳以“真诗”反对“宋人主理”的思想,但那本来就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个性主义思潮的精神之源,在这一点上,我们切不可作割裂观。至于他于明代小说方面所传输的种种信息,同样可以说即时反映了万历间文坛新的文学趣尚。所有这些文学上的信息,又当与许氏接受阳明学,特别如李贽等为代表的左派王学,乃至他1610年入明时接受西方传教安鼎福《天学问答》,《顺庵集》卷一七,木活字本,《韩国文集丛刊》第229册。
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看章培恒师《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思潮》,原载《古田敬一教授退官記念中国文学语学論集》(东方书店1985 年版),转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士的影响,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方可在呈现整个中晚明由中世向近代过渡进程中从思想到文学发生新变意义的同时,进一步阐发许筠在朝、明文化交流的作用。
四、许筠与朝鲜文坛的风气之变
我们再来看许筠接受、传播万历文学信息之于朝鲜文坛的影响。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因限于手头可利用的资料条件,只能在上述相关内容的基础上,作一更为粗浅的探讨。笔者以为,要考察这样一种文学形态的传输与影响,并揭示其文化史意义,更应将之置于整个东亚文学由中世向近代过渡的背景下,从一种相互关联的思想链着手,探究中晚明文学的新质因素是如何逐渐渗透到朝鲜社会内在文化的基础,朝鲜文学又如何以一种文化上的内应力,在迎拒之间予以过滤或吸纳,推动自身逐步实现转变。
如前已述,许筠接受万历文学东传对于朝鲜文坛的影响,比较普遍地被主要定位在进一步推进其时汉诗坛的崇唐之风,这种影响所及,也可以说令其后的诗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仍为明七子一派的天下。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的宗宋或宗唐,确可视为朝鲜中期以来文坛风习转变的一大关捩,少即学诗于荪谷李达的许筠,自己对此持论亦相当鲜明,其在《鹤山樵谈》中即指出:“本朝诗学,以苏、黄为主,虽景濂大儒,亦堕其窠臼。其鸣于世者,率啜其糟粕,以造腐牌坊语,读之可厌。盛唐之音泯泯无闻。”“隆庆、万历间,崔嘉运(庆昌)、白彰卿(光勋)、李益之(达)辈,始攻开元之学,黾勉精华,欲逮古人……由是学者知有唐风,则三人之功亦不可掩也。”不过,当我们已经了解许筠所接受、传播的其实是万历中后期文坛剧变的一种即时、全息的信息时,就应该从整个中晚明文学演进的内在脉络上来理解这种诗风转变背后体现的意义。当初以李梦阳为领袖的前七子,虽倡言复古,但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追求“音之发而情之原”之“真诗”,并且其表现以“比兴”为要。这也就是说,他们主张诗学唐以上,是要学习古人以情感特征为诗歌的本质,宋诗之所以与之前的诗歌划下一道鸿沟,恰是因为其倡理贬情,而这与理学家对文学的要求,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宗唐宗宋之争的背后,实为诗歌应表现真情还是言理、载道之争。虽然前后七子的诗学理论及诗歌创作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出现了所谓“格调优先”而非“性情优先”的偏差,却导致了晚明文学在对其拟古之弊的反省、批判中,重新回到有关对诗歌情感特征的思考,如公安派即是以一种更为强硬的姿态,高举“性灵”旗帜,在主张作家自我性情之真实自然的表现是诗歌唯一本质的同时,将个性及其自由表达视作文学创作的最高原则。这种基于童心说基础上的“性灵”,其内涵恰与一切“闻见知识”相对立。
许筠论诗以“尊唐黜宋”为主的背景与意义,其实亦可作如是观。他对于宋诗作“理语”的激烈批判,正是其逐渐背离朱子性理学的道学文学观的一种反映。在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性理学的全盛期,朱熹之学已成为类似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思辨性文化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日益形上化、道德化,却日益显示出脱离社会、政治环境之日常需要。对此,许筠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近世之所谓学者,非为吾学之可尊也,亦非欲独善其身也……今之伪者,则空游谈,动以伊传周孔事业自期;及其用也,则手足失措,偾而不能自收。
故如前举许氏“宁违于圣人,不敢违天禀之本性也”之论,实际上就是他在认清性理学真实面目的前提下,于所谓“圣人”提出的严苛的道德规范与人的基本欲求发生冲突时表明取舍的宣言,而这也正是他在诗学方面突显关涉文学本质的“性情之道”的一个基点。他也与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主张一样,认为:
尝谓诗道大备于三百篇,而其优柔敦厚,足以感发惩创者,国风为最盛。雅颂则涉于理路,去性情为稍远矣。标准则只在“性情”之表现。尽管他也有文学关乎“世教”之论,但那或许与其实学思想联系起来更为切当。如此来体认许氏的诗学主张与宗尚,便可显现其背后的新质思想,进而显现其在思想史上的突破。他的这种认识与主张,与同时之李晬光(1563—1628)等同调,无论从直接继承、发挥由李梦阳开启,李贽、袁宏道推进的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一面,还是从将李贽所代表的左派王学转换为实学思潮之发端一面,对之后如星湖学派之李瀷,北学派之李德懋、朴齐家,乃至如朴趾源、金正喜等,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梳理这一条线索的曲折发展,自然也就能够从思想文化的总体,进一步探明朝鲜文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轨迹及特点。不仅如此,许筠这种认同于李梦阳所开创的“真诗在民间”的人文主义思想,还可与他接受王阳明诸如“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学说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如何在宣导平等观念的同时,赞赏用“常语”创作的“俗讴”,这与袁宏道宁可欣赏《擘破玉》、《打草竿》等民歌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加上他自己如何在《水浒传》等明代通俗小说的影响下,创以用谚文撰作小说,从而相当鲜明地表现出随着思想的革新、汉文学的革新,带来民族语文学上升这种近世文学的共同特征。
五、结 语
以上是对许筠与朝、明文学交流所作的再检讨,宗旨已如前述。鉴古是为了知今,处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已日益认识到文明的进步与和谐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曾经高度一体化的东亚社会,如何在公正、和平的原则下,携手致力于各自民族文化内质向更为积极的方向更新、提升,并积极推进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有鉴于此,试图从文学一侧追踪整个东亚社会由中世向近代过渡、演进的轨迹,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
(原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
第19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