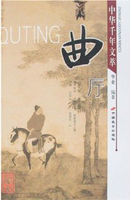家,是多么美丽甜柔的一个名词。
征人游子,一想到家,眼里会充满了眼泪,心头会起一种甜酸杂揉的感觉。这种描写,在中外古今的文里,不知有多少,且不必去管它。
但是“家”,除开了情感的公子,他那物质方面,包罗的可真多了:上自父母子女,下至鸡犬猫猪;上自亭台池沼,下至水桶火盆,油瓶盐罐,都是“家”之部分,所以说到管家,那一个主妇不皱眉?一说到搬家,那一个主妇不头痛?
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
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
新近因为将有远行,便暂时把我的家解散了,三个孩子分寄在舅家去,自己和丈夫借住在亲戚或朋友的家中,东家眠,西家吃,南京、上海、北平的乱跑,居然尝到了二十年来所未尝到的自由新鲜的滋味,那便是无家之乐。
古人说“无官一身轻”,这人是一个好官!他把做官当做一种责任,去了官,卸了责任,他便一身轻快,羽化而登仙。
我们是说“无家一身轻”,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责任,不必想菜单,不必算帐,不必洒扫,不必哎哟,“不必”的事情就数不清了。这时你觉得耳朵加倍清晰,眼睛加倍发亮,脑筋加倍灵活,没事想找事做。
于是平常你听不见的声音,也听见了;平常看不出颜色,也看出了;平常想不起人物和事情,也一齐想起了;多热闹,多灿烂,多亲切,多新鲜?
这次回到南京来,觉得南京之秋,太可爱可怜了,天空蓝得几乎赶得上北平,每天夜里的星星和月亮,都那么清冷晶莹的,使人屏息,使人低首。早晨起来,睁眼看见纱窗外一片蓝空,等不了扣好衣纽,便逼得人跑到门外去:在那蒙着一层微霜的纤草地上,自在疏情的躺着十几片稀落的红黄的大枫叶,垂柳在风中快乐的摇曳,池里的凤尾红鱼在浮萍中间自由唼喋着,看见人来,泼剌地便游沉下去了。
这一天便这样自由自在的开始。
我的朋友们,都住在颐和路一带,早起就开始了颐和路的巡礼,为着访友,为着吃饭,这颐和路一天要走七八遭。我曾笑对朋友说,将来南京市府要翻修颐和路的时候,我要付相当的修理费的,因为我走的太多了。
朋友们的气味,和我大都相投,谈起来十分起劲,到了快乐和伤心时候,都可以掉下眼泪,也有时可以深到忍住眼泪。本来么,这八九年来世界,国家,和个人的大变迁,做成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多少甜酸苦辣的情感。这九年的光阴,把我们从“蒙昧”的青春,推到了“了解”的中年,把往事从头细说,分析力和理会力都加强了,忽然感到了九年前所未感觉到的悲哀和矛盾――但在这悲哀和矛盾中,也未尝没有从前所未感觉到的宁静和自由。
谈够了心,忽然想出去走走,于是一窝蜂似的又出去了。
我们发现玄武湖上,凭空添出了八个幽静清雅的角落,这里常常是没有人,或者是一两个无事忙的孩子,占住这小亭或小桥的一角。这广大的水边,一洗去车水船龙的景象,把晴空万里的天,耀眼生花的湖水,浓纤纤的草地,静悄悄的楼台,都交付了我们这几个闲人。我们常常用宝爱珍惜的心情走了进来,又用留恋不舍的心情走了出去。
不但玄武湖上多出许多角落,连大街上也多出无数五光十色、眩目夺人的窗户。货色是件件便宜,样样新鲜!好久不开发家用了,仿佛口袋里的钱,总是用不完,于是东也买点,西也买点,送人也好,留着也好,充分享受了任意挥霍的快感。当我提着、夹着、捧着一大堆东西,飘飘然回到寓所的时候,心中觉得我所喜欢的不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糖果,乃是这糖果后面一种挥霍的快乐。
还有种种纸牌戏:十年前我是决不玩的,觉得这是耗时伤神的事情。抗战以后,在寂寞困苦的环境中,没有了其他户外的娱乐,纸牌就成为唯一的游戏。到了重庆,在空袭最猛烈的季节,红球挂起,警报来到,把孩子送下防空洞,等待紧急警报的时间也常常摊开纸牌,来松弛大家紧张的心情。
但那还是拿玩牌当作一种工具,如平常大学教授之“卫生牌”,来调和实验室里单调的空气。这次玩牌却又不同了,仿佛我是度一种特别放纵的假期,横竖夜里无须早睡,早晨无须早起,想病就病,想歇就歇,于是六七天来,差不多天天晚上有几个朋友,边笑边谈,一边是有天没日的玩着种种从未玩过的纸牌花样。
这无家之乐,还在绵延之中,我们还在计算着在远行之前,挤出两三天去游山玩水。但我已有了一种隐稳寂寞的感觉!记得幼年在私塾时期,从年夜晚起,锣鼓喧天的直玩到正月十五,等到月上柳梢,一股寂寞之感,猛然袭来,真是“道场散了”!一会儿就该烧灯睡觉,在冷冷的被窝中,温理这十五天来昏天黑地的快乐生涯,明天起再准备看先生的枯皱无情的脸,以及书窗外几枝疏落僵冷的梅花。
上帝创造蜗牛时候,就给它背上一个厚厚的壳,肯背也罢,不肯背也罢,它总得背着那厚壳在蠕动。一来二去的,它对这厚壳,发生了情感。没有了这壳,它虽然暂时得到了一种未经验过的自由,而它心中总觉得反常,不安逸!
我所要钻进去的那一个壳,是远在海外的东京。和以前许多的壳一样,据说也还清雅,再加上我的稳静的丈夫,和娇憨的小女,为求安取暖,还是不差!
是壳也罢,不是壳也罢,“家”是多么美丽甜柔的一个“名词”!
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南京颐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