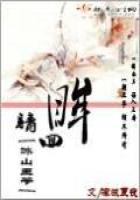7
雷声一直跟着我来到了城里。雷声如同戴在我头顶上的帽子。雷声像我的尾巴,像我的脚步声。天还没有完全亮透,我注意到大街两旁有几个穿黄外衣的人,手里拿着笤帚,在路面上划过来划过去。他们是在写字么?我好奇地走向最近的那一位黄衣服,是个女的,年纪不小了,头上戴了个白色的帽子。我问她在干什么。她瞪了我一眼,对我说道,你看我在干什么。我说你在写字吗,你真是个好学生。她又瞪了我一眼,然后叉起膀子咯咯地笑了起来,她的笑声仿佛生完了蛋的母鸡。我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呢。她摆着手说“不好笑,不好笑!”,可是她却笑弯了腰。她的笑声引来了另外几个穿黄外衣的人,一个是男的,还有三个是女的,他们和这个女人交流了几句,然后一齐笑了起来。我这个人呐,既见不得人家哭,又见不得人家笑。所以,我准备离开了。我说,我要办事去了,没工夫陪你们玩了,你们在这里慢慢笑吧。刚走几步,先前的那个女人过来拉住我的袖子,问我要办什么事。我说找人。
谁呀?
许花子。
许花子是谁?
她不是谁,以前她是神仙,现在可能不是了,我心里没底。
那你到哪儿去找她呢?
上面,我回答道,然后随手指了指附近的一座高楼,这座楼房实在是高啊,从下面往上看几乎看不到它的顶,而且楼面全是用玻璃做的,在清晨的光线里闪闪发亮。
那上面?
是啊,上面。
你在撒谎吧?我知道,那上面不是你这种人能够去的地方,不仅你去不了,连我们也去不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因为它是座高楼。
我说,高楼有什么稀奇的,我还上过天呢。
他们都笑了。笑过后,那个女的对我说,你去试一试吧,如果上不了,就回来跟着我们一起扫地,反正我们这里也缺人手。
本来我是没有打算去爬那座高楼的,现在听他们这样说,我还真的是动了心,去就去,说不定许花子真的在那座楼房里呢。我朝它走去。我以为它就在附近,可是走了半天,它还距离我那么远,好象我永远走不到它面前一样。天已经亮了,但没有太阳,太阳被困在了云雾里。空气很闷热,没有风。我沿着马路走了一段后,回头发现许多人都跟在我身后,我有点生气,于是拦住其中的一位,问道,你们为什么都跟着我?那人不耐烦地推了推我,说道,去去去,滚一边去!谁跟着你了?神经病!但我还是不甘心,你明明跟着我在走嘛,我说,难道你也要去找许花子么?滚开!这次,那人使上劲,一掌就将我推到了马路中间。刚好驶过来一辆车,差点压住了我的脚趾。找死啊!司机伸出头骂了我一句。我越发生气,就去找刚才那个推搡我的家伙,可是他已经跑远了。我高声喊道:你等等!给我站住!但那家伙不仅没有站住,而且越跑越快,转眼就消逝在了街角边的一排矮房子里面。
当我追赶那个人的时候,来了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他们很快就逮住了我,一左一右抓住我的肩膀,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想撒野吗?我说,刚才的那个人差点把我推到了车空里。他为什么要推你呢?你们以前认识吗?警察问。我说,不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他呀,但他老跟着我,我不让他跟,他就推了我一下。警察说,你跟我们去派出所一趟,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给我们说清楚。我说,我有事要办呢,没有时间陪你们了。但他们不理我,架着我就走。
我被两个制服带进了一个房间,他们让我先一个人在里面呆一会儿,结果这一呆就是一整天,直到外面和里面全黑定下来后,才来了另外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带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我看见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放了一盏灯泡很亮的台灯,台灯旁有一只碟子,碟子里面装有两个白馒头。我又渴又饿,一见到馒头就直奔过去。这时,有一只手从桌子那边伸过来按住我的手,说道,别急,先交代问题,说完了再吃。我这才看清楚台灯后面另外还坐着一个人,穿着同样的制服,只是没有戴帽子,花白的头发向后脑勺齐齐地梳着。
我说,我饿了。
我说,我渴了。
我说,别用那么亮的灯泡照我的脸好不好,那东西比太阳还毒呢。
我说,能不能先给我杯水喝?
没戴帽子的那个制服脸上始终带着笑意,我都快要哭了,他却一直在笑。我侧了侧头,想避开灯光看清楚他的脸,但他就是不让我看,他把台灯举在手里,让灯光紧紧盯住我的眼睛。我觉得难受之极,干脆哭了起来。
我哭啊哭,直哭得鼻歪眼斜,口干舌燥,才听见那人慢条斯理地嘀咕了一句:哭够了吗,哭够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我抽噎了一下,点点头。
姓名?他问。
傻瓜,我回答。
那人放下笔,冲我吼道,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你在玩我呢,你说谁是傻瓜?啊!
我说,我没空玩啊,我要找许花子呢。
谁是许花子?
许花子以前是神仙,现在不知道她还是不是……
是个屁!他霍地站了起来。
我一下子看清楚他的脸了,他的脸好丑啊,鼻梁是塌的,两只眼睛隔得那么开,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丑的人。
我看见你的脸了,我笑道。
那人听见我的话后赶紧坐回到了台灯后面,他把笔杆夹在指缝里转动着。我看你还是老实交代吧,要不然的话,是对你没有好处的,他说。
我问交代什么。
别装蒜!他呵斥道,你先说说你来这里的目的。
我说,村子里没有水了,井里面全干了,我是进城找许花子帮忙的。
许花子是你什么人呀?
我说,我们曾一起上过天。
胡说八道!
我说,是真的。
你莫非是个神经病吧?
我说,我不是神经病,我是傻瓜。
傻瓜啊,你说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没有!告诉你,反抗是没有出路的,多少人曾经想在我们面前装疯卖傻,最后还不是一样老老实实地招供了么?
招供什么?我问。
去你妈的!这回,这家伙好象真的发脾气了,他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把桌子也掀翻了,台灯晃了晃,几乎就要落到地上。我连忙伸手去接。“去你妈的,给老子滚!”他推了我一把,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他说。
于是,我就滚了出来,很快就滚到了街面上。
街上像失了火一样,火光东一簇西一簇的,到处都在冒青烟,许多人站在马路边的烟雾中,手上拿着一根根棍子津津有味地啃着。空气中飘荡着烤肉的香味。我决定过去看个究竟。当我走到冒烟的地方时才发现他们果真是在烤肉吃。肉被串在一根根细铁丝上面,抹上一些粉末,放在一只装有白碳的铁盒子上来回翻烤着。有一位小女孩等得不耐烦,就一个劲地问她身边的女人:“妈妈,怎么还没有熟啊!”女人个头高大,穿着无袖连衣裙,两只膀子交叉着抱着胸前,胸脯高高耸立,仿佛两座山包。我站立在她们背后,瞧着女人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心里也产生了一股吃肉的冲动,口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也许是我口水滴落地面的响声惊动了她,女人回过头了看了我一眼,问道,你也想吃羊肉串么?我点点头,笑了笑。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想有什么用。我在心里丈量着“想吃”与“吃进嘴里”之间的距离,不免感到沮丧。
那女人好象看懂了我的心思,当她再次回头打量我时,问了我一句:哎,你是不是忘了带钱?
我回答道,我没钱,我已经饿了一整天了。
是吗?她又上上下下看了看我了几眼,笑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吃,反正多一张嘴少一张嘴都是一回事。
小女孩揪了揪她母亲的裙角,悄悄问道,妈妈,那个人是谁呀?
她的话被我听见了,我回答说,我是傻瓜。
傻瓜?她们齐声笑了起来。
一个自称自己是傻瓜的人绝对不会是傻瓜的,女人笑过以后,说道,我看你的模样是从外地来的,能告诉我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吗?
我老实承认道,我是来找人的,我要找的那个人叫许花子,我想找她帮我打一口井,我们村的井水都干了。
打井?许花子是干什么的,听名字好象是个女的呢,她说。
是女神仙,我说,这么说吧,她曾经是个神仙,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的了……
神仙?女人笑着摇摇头,说道,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是个会撒谎的人,果然不会啊。好了,来,让我们边吃边聊吧,这羊肉冷了就不好吃了,女人将几根细铁丝递到我手里,又递给小女孩一根,然后自己才拿起另一根,侧着脑袋细嚼慢咽起来。而我,却是在狼吞虎咽,三下两下就将铁丝钎上的肉卷进了肚子里。
好吃吗?女人笑眯眯地望着我,问道,还吃不吃?不等我回答,她就扭头去招呼那位烤肉串的男子,再要二十串,她说。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晚上我总共吃了多少串肉,我记得吃到最后嘴唇已经没有任何知觉,肚子嘛倒还是可以承受的。在我吃的时候,她们俩一直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我,那个女孩不停地问道,妈妈,这是第几串了?那个女人却不回答,只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肉串太辣了,我的眼泪鼻涕直往下流,女人就在一边不断递纸给我,我的脚下已经扔了无数个纸团,这些纸团像雪片似地渐渐覆盖住了我的脚背……
女人将我从雪片中拉出来,带我去附近的一个小卖部买水喝。水都是装在瓶子里面的,从一个冰窖般的铁柜子里拿出来,握在手心里十分冰凉。我一口气喝了三瓶。这时,我就听见肚子里面传出了咕咕的响声。
饱了,我讪笑道,这回真的是饱了。我拍打着浑圆的肚皮,跟随在女人和孩子身后,朝一条僻静的巷道深处走去。
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我几乎就要忘记进城里来的目的了。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为什么会跟这个陌生的女人回家,而且还在她家里心安理得地一住那么多天?我在这个女人家里学会了洗澡,不是一般的洗,而是大洗。每次,女人都要将水满满地放进一个白色的大瓷盆里,瓷盆极其光滑,稍不小心就可能在里面摔上一跤。水是从一个铁管子里面放出来的,清亮,而且是温热的。瓷盆将近我一人长,我爬进去,整个身子都浸泡在水中,只有脑袋露在盆沿上呼吸。我第一次面对这个瓷盆时有点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就坐在盆沿上发呆,偶尔用手掌撩起几滴水浇在身体上面。我脱光衣服,坐在腾腾的雾气中,感觉到飘飘欲仙,有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类似于置身于天堂上的幻觉。后来,我就听见了笃笃几下敲门声,接着是女人在问:
“你在干什么?”
我哼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怎么不说话?需要帮忙吗?”
我又哼了一声。
这时候,门裂开了一条缝隙,如同一个人张开嘴巴,我感觉到一丝凉意。而当这张嘴巴慢慢靠近我时,凉意消逝了,变成了一团热气。我透过浓雾看见女人站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的浴巾。
你怎么不洗啊?她好奇地看着我问道。
我说,我这不是在洗吗?
女人用一只手掌护着嘴,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浑身直颤,身体也摇摇欲坠。我担心她跌倒在了瓷盆上,就起身用手去扶她,她却一把将我推倒在了瓷盆里面,水花溅起老高,打湿她的连衣裙,将她淋成了一只落汤鸡。我幸好用手臂扶了一下盆沿,否则我的后脑勺一定会磕碰在墙壁上。
你干什么?!我生气地问道。
女人止住笑,走到盆沿边蹲下来,说道,你从来没有这样洗过是不是?你不会洗澡是不是?你应该将身体泡进盆子里才是,对,就像这样,全部泡进水里,只露出脑袋在外面呼吸。哦,水少了一点,让我再给你加满吧。说着,她便拧开龙头,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我感到自己慢慢地飘浮起来。
在我往上漂浮的时候,有一双手在上面牵引着我,我感到从我的身体里面渐渐长出了一根绳子,我感到这根绳子被那双牵引我的手不断地搓揉着,越来越粗大,越来越结实,它完全可以把我悬挂在空中。我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四仰八叉地悬浮在云雾弥漫的半空上面,缓缓向极乐世界飘去……
从此,我便对洗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再也无法离开这只大瓷盆了。
每天我都睡在瓷盆里面,等待女人把香喷喷的饭菜端到我的面前来,除了撒尿和大便外,我几乎从不离开瓷盆半步。女人对此似乎也没有任何怨言。我不知道她是谁,她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我也懒得去了解。如果不是她那天主动告诉我她的名字,我恐怕永远也不会去问她的。那天,她也挤进了瓷盆,折着身子趴在我身旁,问道,你难道不想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待你?
我懒洋洋地恩了一声。
女人说,你这个傻瓜呀,唉,还是我来告诉你吧,我叫侯小云,现年三十八岁,丈夫在三年前跟另外一个骚女人跑到南面去了,留给了我这套房子和一大笔钱,这笔钱足以让我这辈子衣食无忧。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人我为什么不找却偏偏把你这个傻瓜带回家呢?你知道吗,我现在信不过任何男人了,他们嘴里说爱我,实际上都是在爱我的钱财。我看得出来,只有你是个例外。是不是,傻瓜?
我又懒洋洋地恩了一声。
女人说,我现在是彻底想穿了,什么情啊义啊的,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觉得这话我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但想了好久才想起来,是明清对我说的。明清当时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说,现在我谁也不相信了,只信任你这个傻瓜。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他不是感到后悔了么?后来他不是说我也在欺骗他么?想到这儿,我摇了摇脑袋,说道,不是的。
什么不是的?侯小云问道。
我说明清也是这样说的。
明清是谁?她问。
明清是谁?我问自己,我发现我并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来。那么,明清究竟是谁呢?我努力回想着,结果发现明清已经不知什么时候跳出了我的脑海,变成了一个恍惚的无法勾勒的轮廓。然而,当我呼吸的时候,我闻到了他的气味,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又看见他在我的体内上蹦下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再次摇了摇脑袋,就突然想到了那天晚上见到的那位漂亮的小女孩,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了,我问侯小云:那孩子呢?
你说芬子啊,哦,她是我妹妹的女儿,平时也喊我妈妈,两个妈妈,多好!女人说着,又将自己的身体往我身边贴了贴,说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妈妈的孩子是多么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