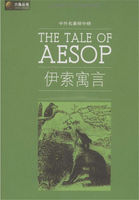莫奈眉头皱皱,眼泪就不可抑制地掉下来。
杜渡有些慌。
她努力地吸着鼻子,哼唧着说道:“为什么都是豆腐呢?”
其实是想说,你干吗对我那么好!
她擦了擦鼻涕,像审问犯罪嫌疑人一样犀利地问:“你喜欢我什么?”
杜渡像被她吓到了似的,反倒很直接地说:“漂亮。”
她有些意外,鄙视地斜眼看他:“男生都这么俗吗?”
他红着脸不安地解释:“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你涂了大红色的口红,很惊艳。”
他太紧张,没有把话说全。
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在刚入学不久,她穿白色的裙子,却涂了最红的唇膏,张扬又夺目,旁边的学长说这种女生属于“甲醇”。听起来是有些变味的玩笑,有人跟着笑起来。他忍不住回头再看她,却看见她俯下身,逗弄着一只流浪猫,手心里是给猫咪准备的香肠。
不知道为什么,就对那个场景念念不忘,他固执地认为,这个女生骨子里只有温柔与慈悲。
莫奈抢过杜渡手里的菜单,挑剔地说:“那就吃海带豆腐吧。”
那次之后,她和杜渡的关系渐渐不一样。他在她心里,像朋友也像家人。甚至,从来不对外人说过的话,她也会讲给杜渡,包括她的家族病,包括她对生命的惶恐。
他总是静静的,像个树洞,保守她的秘密,又包容她的坏脾气。
她说,我可能是快死了吧,所以上天才派个天使来安慰我,杜渡啊,你真是我的天使啊。
她说,喂,天使,你有没有带橡皮擦呀,我心里有个名字擦不掉。
她说,喂,你知道吗?我心里那个人是个混球,可是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办呢?
她说,喂,我每天提路云陌你都不会烦吗?你有没有骨气啊?你应该拍屁股走人才是啊!
她对他吼,有恨铁不成钢的怒意。
他也只是推推眼镜,哼都不哼一声。
她恨自己,心里擦不掉的名字竟然是“路云陌”三个字。
有人把真心给了你,你却视而不见,反倒向更冷漠的人去讨要真心。莫奈觉得,这种纠结的逻辑,即是逃不开的命运。
她对命运,已经臣服。
心脏第二次出问题,是在三月开学不久,这一次她真的有些害怕。
她很认真地说:“杜渡,我真的要死了。”
那个男生一向讷言,听她说完,也只是淡淡地说:“我会一直在你旁边的。”
我会一直在你旁边的。这是她听过的最动人的一句话,但却不是情话。
10
莫奈的伤势已渐平稳,路云陌请了国内顶尖的整容科医生来会诊,要针对莫奈的心脏情况给出最稳妥的手术计划。
宫九在审讯中突然毙命,据说,他死前似乎出现幻觉,大喊着朴娓蓝的名字,脸上布满恐惧。法医鉴定,他曾经吸食过量的致幻剂。
四月一日,朴娓蓝的祭日。宫九死在了朴娓蓝祭日的前一天。
纪瓷只知道江恩宝将朴娓蓝的骨灰埋在了安城,却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每年四月一日,她都去白树镇,陪着金婉芬。孤单而糊涂的母亲,依然能记得这是女儿的生日,她会亲自给纪瓷煮红鸡蛋,在她脸上滚三圈。
今年,纪瓷照例在出发前去了趟蛋糕店,订了朴娓蓝生前最爱吃的水果蛋糕。
到养老院的时候,金婉芬已经早早地等在大门口,而她一旁是静默站立的江恩宝。
她并不觉得意外。
江恩宝亦然。
金婉芬仍旧望着纪瓷身后,似乎有些遗憾:“娓娓啊,书生没和你来啊?你们没吵架吧?”
纪瓷笑着安慰她:“他在忙啊,他说忙完了来看你。”
江恩宝看一眼纪瓷,显然,金婉芬那一声“娓娓”触动了他。他只知道纪瓷这些年一直在照顾金婉芬,没想到她默默地充当着娓娓的角色。
金婉芬又指着江恩宝,小声地说:“他是你哪个朋友啊?他这些天总来。”
纪瓷解释道:“他是恩宝哥啊,对娓娓很好的恩宝哥。”
“哦,恩宝。”金婉芬点头。
江恩宝擦擦鼻子,双手插在口袋里,跟着他们两个在路边转悠,一边走一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
金婉芬不时回头,看看他,然后偷笑着和纪瓷耳语。纪瓷回头看看江恩宝,也笑起来。
“喂,你们刚刚笑什么?”江恩宝走到纪瓷身边不着头脑地问。
“阿姨说喜欢你,看着就像他儿子一样。”
说完,纪瓷又笑。笑得江恩宝浑身不自在。他瞪她一眼,索性快步走到前面,将金婉芬背起来在地上转圈。金婉芬吓得直尖叫,但是马上又极开心地笑起来。
三个人在小镇静寂无人的路上,疯疯癫癫地玩闹着,像小孩一样。
那天,他们一起吃了蛋糕,煮了鸡蛋,金婉芬照旧用鸡蛋在纪瓷的脸上给她滚运。
直到午饭后,金婉芬玩累了,沉沉睡了。
江恩宝说:“其实,她一点都不糊涂,她知道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她的娓娓了。她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
纪瓷用手轻轻摩挲着金婉芬的掌心。是那样吗?所有的母亲都会对自己的儿女有与生俱来的敏感。
她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不愿意承认最爱的女儿再也回不来了。
江恩宝轻轻起身:“我带你去后山走走吧。”
四月初的北方,仍旧是荒凉的景象,向阳的山坡上会有稍稍清浅的绿意。但风是不冷的。
江恩宝也不说话,只是沿着山路徐徐疾行。
到了山顶,他停在一小抔黄土堆前,弯下腰,把杂草除了除。
纪瓷看着那小小的坟头,似乎已经明白了。
她立刻也蹲下来,一边拔草一边吸着鼻子,眼泪大滴大滴地落在黄土上。最后,她索性坐下来,放声大哭。
“你看,这么些年,娓娓一直在这里看着呢,她能看到你为她妈妈做的一切。”
江恩宝淡淡地转身,在平地上坐下来。这里视野开阔,可以望见整个小镇,其中有着瓦蓝屋顶的就是养老院的房子。
纪瓷还是忍不住眼泪,坐在他旁边,仍旧不停地抽泣着。
原来,朴娓蓝一直就在离她不远的地方。
“纪瓷,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江恩宝拧着手里的枯草,“当年,从火灾里把你救出来的人,不是我,是林斐。”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林斐已经抱着昏迷的你跑到了离安全门两三米的地方,但是,很不幸的是,有一块天花板掉下来,他挡了一下,你们俩都摔在地上。我冲过去,他让我先把你救出去。所以,记者们拍到的就是那样一幅画面,我抱着你,把你交给随后而来的消防员。”
“林斐很快也被救出来,和你一起送进了医院。但是,很不幸,他伤到了眼睛。其实,他把娓娓送出来再转身去救你的时候,眼睛就已经是模糊的了,他是摸索着找到了你的位置。医生说,如果他不再次进入火场,也许视神经还不会完全坏死。”
纪瓷一动不动,眼角的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脸上的泪痕被风吹过,干干的,很不舒服。
江恩宝掏出一个信封,递到纪瓷手里,然后起身:“这是当年整理娓娓遗物时发现的,它的主人应该是你,我替娓娓向你道歉。我自己也很抱歉,过了这么久才把一切讲出来。纪瓷,你的罪就到此结束吧。”
江恩宝头也不回地下山而去。
纪瓷在山风里坐了许久,她等待着,耳畔却再没有轰轰的鸣声,她再也听不见朴娓蓝咯咯的笑。文老先生治好了她的耳病,她却因此觉得异常孤独。
良久,她打开那封信,跃入眼帘的是熟悉的林斐的笔迹。
这封错失的告白信,在经年之后,在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之后方才辗转到达真正的收信人手里。
她安静地读完,默然起身。望着天边的夕阳,心里涌起的是难言的疼。
最在乎的人,总在误会与错过之间擦身。不能怪命运不公,是你没有交付出足够的信任,是你没有为爱情义无反顾的决心。
电话在静寂的山间突兀地响起,是室友黄霄打来的。
黄霄在电话那端惊诧地呼喊着:“纪瓷,莫奈自杀了!天啊!太可怕了。”
纪瓷的手猛地一抖,电话险些落地,她匆忙地往山下跑,另一只手里的信纸簌地被风带走了。
被带走的岂止是一张纸,是她后知后觉的所有的悔与愧。
她已然不在意,也无法在意。时间的河浑厚无情,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谁能逆流而上,把往事追回来?
11
莫奈是在拆除绷带的前一天自杀的,在那间高级的VIP病房里,她用输液管勒死了自己。
第一个发现她的人是路云陌。
那一天,她找了借口让杜渡离开,然后给路云陌打了个电话。她约路云陌来医院看自己,鲜有地撒着娇,让他给自己买林记的米线。
林记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米线店,在一中旁边的外贸胡同里,她曾经带路云陌去过一次,路云陌看了看那间寒酸的店面,转身就走。
她在他身后细细想来,她与他在一起的时光,除了纸醉金迷,并无半点市井的烟火气息。
如果突然就死掉了,这算不算是留在人间的遗憾呢?
她并不能肯定路云陌会去林记,穿街过巷,挤过熙攘吵杂的人群,只为了给她买一份小吃,她对路云陌的爱情从来都没有信心。
他绝对不会爱任何人。因为,他最爱的是他的姐姐。莫奈叹口气。
然后,在等待路云陌的时间里,她拿出纸和笔,开始给他写信。
她写“我爱你”三个字,写完自己仔细端详,撇撇嘴,又撕掉。再写一遍,仍旧撕掉。她觉得“爱”字好难写,怎么写出来看着都是丑的。
最后,她只写了一句话——愿来生,我们都能有平常人的幸福。
然后,她很镇定地把输液管拔掉,走进了卫生间。
她这一生都狂热地爱着漂亮的衣服,但最后这刻,却只有一套粉白相间的病号服,干干净净的,还带着消毒液的味道。她看着镜子里的脸,缠满绷带的脸,对自己说,还好,这样死掉就不会担心看到绷带拆除之后的丑样子了。
对于死亡的恐惧,从童年就横亘在她的生命里。
但真的到了这一刻,她反倒异常的平静。
她从容地踩在马桶上,衣服上有小小的纸片掉下来,像一棵树最后的一片叶子,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辨认出,那是“爱”字的一部分。
一刻钟之后,路云陌来了。
他手里的米线盒掉在地上,浓稠的汤汁溅满了他的鞋尖。米线的香气在房间里漫溢,是莫奈向往的市井味道。
纪瓷在吊唁的人群里看见路云陌。
路云陌恨恨地对纪瓷说:“她以为她很聪明吗?她以为这样我就会一辈子记住她吗?”
纪瓷已经哭不出来眼泪,她的脸上无悲无喜,她平静地对路云陌说:“难道不是吗?你这辈子再也不会忘记这一幕吧?”
“我恨她。”路云陌咬着牙说道,“我人生里爱过的两个女生,竟然选择了用同一种方式离开。我恨她们每个人。”
他穿过人群,丝毫不理会近在咫尺的那些悲伤哭泣的人们,仿佛他们的悲戚与他毫无关系,仿佛他从不曾认识过躺在冰棺里的那个女孩儿。
纪瓷静静看着路云陌离开。
那么庞大的“恨”,她也曾有过,并且一直充盈在心间。
但这刻,看着路云陌的背影,她忽然困惑起来,那真的是恨吗?
她看见杜渡在人群里穿梭,忙东忙西,帮着莫奈的亲人安排后事。那个男孩子,好像不是她记忆中容易脸红的羞怯样子,他沉着冷静,就仿佛莫奈虽然离开了,他却依然可以是她的依靠。
爱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但究竟哪一种才是对爱情最好的诠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