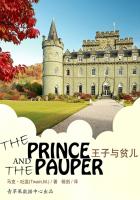那天夜里,岂容答应了会都里的老板皓仲,每周,用两个夜晚,在那里做琴师。
会都里就开在音乐学院的西门斜角上,粉绿色的一栋小楼,楼下是餐厅,楼上是酒吧,皓仲是永和人,长得却白净斯文,戴一副碳素框眼镜,常年都是烟灰色西装,留一撮小胡子,头发服帖。他第一次见到岂容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刚到上海,从租住的二楼大套间窗口看出去,隔了稀散的水杉,楼上就是一张素白小巧的脸。这个女子头发瀑布般,上半身裹了件乳白色背心,正探出脑袋来晒一张猩红色的地毯,那是个雨后的晴天。
皓仲常常会在喝红酒的时候想起岂容的脸,当时,他也端着一小杯红酒,试图看这座城市雨后的天,和台北不同的消尘清朗。岂容探出脑袋来,张开地毯利落地挂了出去,她没有遮掩身体,俯身而出的时候,皓仲甚至可以隐约而见她紫色的棉内裤,或者,还有乳沟,是小而坚挺的脉络,沉浮里勾勒了曲线。那样的午后对他而言太清晰了,四月天,霾霾清明雨后太阳疏淡的微粒,密布在身体周围,还有那张素白的脸,和不经修饰的身体。
他当时看着,心不自然地惶惶起来,胸口像被猫爪挠了一下。他觉得从那天起,自己就爱上了这座城市,这个女子,还有他们共同租住的这栋老楼。
真好,他想。
这又是三月,皓仲来到上海的第四个三月,岂容已经在会都里做了大半年的琴师,每个周六和礼拜日,她都穿着朴素到显了清贫的衣服抱着琴谱走来。皓仲允她极少的固定薪水,除此之外,收入全依赖小费,可岂容和其他琴师或歌手不同,她很少笑,很少向客人表示感谢。收工下班的时候,她从钢琴前站起来,抖开原本夹在琴谱中的小布包,然后端起玻璃瓶将钞票倒进去,像是吐纳污物般再收起布包,合好琴谱,离开。已经有不少客人向皓仲抱怨过这个女琴师的古怪,他们建议他把她出场的轮次安排在非周末,那她爱谁谁就爱谁谁去吧,用不着花钱还看人脸色。
皓仲恭谦地向客人道歉,也语气平缓地与岂容谈,可他仍不舍得将她安排在生意清淡的非周末,因为那样,她的收入会缩水一大半。有时候,岂容会记得皓仲的话,她在客人投入小费的时候莞尔一笑,于是昏黄灯光下,原本素白的脸变得苍白,她头发流泻下来,嘴唇上扬,表情仍是没有的,模样实在有些骇人。
连疼惜着她的皓仲都觉得骇人。
岂容索性还是不笑了,她愣愣地弹,愣愣地活。有客人私底下打趣说,这女琴师多像个女鬼啊,这么白,这么瘦,琴弹得固然好,却飘忽得很,你看她走起路来也是无声无息的,你说她会笑么?她会说话么?
这样的话传到岂容耳朵里,她自己也不禁纳闷起来。是从什么时候起,她极少与人交谈,极少说话,极少有喜怒哀乐?她想不起来。记忆似乎被剜去一整块,总在跳跃里接壤边境。她想起姐姐岂言的脸,那是多么明艳的脸,若是岂言在这儿谋生活。她的笑一定非常值钱。
岂容也会对自己是否真的已经是个女鬼产生质疑,有时候她在夜里走回家,会不经意地站到路灯下,回头寻找自己的影子,还好还有影子,长长的一斜;她试着随腊冬里的风跑步,顺着跑,看看自己能不能飞起来,女鬼不是都能飞的么,可她飞不起来。这样空寂的夜里,在疏落无人的马路上,岂容的动作看上去就像个孩童,她想起小时候和姐姐追逐在放学路上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手里举着吃剩了两颗的糖葫芦。
姐姐,姐姐。这是个岂容喊起来会心疼的词。在她痛觉中枢神经末梢损伤后的十年里,心疼是唯一还能感知的痛觉。
有时下班收工,皓仲会开车送岂容回家,他们住在同一栋老楼里,岂容的三楼,他的二楼,是最具理由的顺风车。可路上,两个人几乎都是沉默的,皓仲放一些轻音乐,这么悄无声息地开上十分钟,然后停车,下车,各自回家。所以更多时候,皓仲只喜欢将车子开在岂容身后走,不被她发现。他靠在椅背上透过挡风玻璃里远远地看,等到岂容就要从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再次启动,跟上去,如此往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到这个素白羸弱女子的另一面,她也可以欢跳,也可以像个孩子般在路灯下捕捉自己的影子。
在城市夜最明媚的时候,那是另一个岂容。
皓仲还记得三年半前自己第一次下定决心和那个总在天雨过后晾地毯的女子搭讪时的情景,那是夏天,她趿了两只款式不同的拖鞋第一次在下午下到楼下,为难地向上看着,老楼屋顶的水管裂开了一道口子,水箱里的水似瀑布般倒下来,打湿了一整片窗棂。她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跑去电话亭边拎起电话又放下,似乎并不知道应该找谁。正巧遇上皓仲下楼买烟,只穿了蓝条纹裤衩没戴眼镜,头发蓬蓬地看见她就走了过来。他停在岂容身边,说:“先关窗吧。”然后走到客堂底楼去敲房东家的门。“笃笃”地敲开,递上新买的烟,让房东老伯去居委会找人来修。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岂容也记得那一天,仲夏午后突然跃入屋内的清水,湿了窗棂揉了窗帘,打得地砖上一片狼藉。她似乎没穿乳罩就这么跑下去了,趿了不同的拖鞋,“嗒嗒”踩着木楼梯奔下去,她以为房子裂了,或者根本,是天裂了。好端端的晴朗,突然遭此劫难。只是,她记不得皓仲出场时的模样,在阳光底下的模样,笼了烟水只一个轮廓走来,然后是潮湿客堂间里他的背影,男人的背影。她再也不敢看下去,双手环抱趿着拖鞋闷头跑回屋子,关窗,绞干窗帘,撑一支竹杈在窗台上,任它自由风干。
那时候岂容还有最后一年的课程,她已经开始日夜颠倒,只在夜里去到琴房,脱得剩下薄翼般的内衣,发疯似的敲击。母亲娇贵搬回了原来的屋子,隔三差五过来为她做一顿饭,留下生活费,然后再次离开。
面对这样的离开,岂容已经习惯,十三岁那年,她面对姐姐岂言的离开,十四岁那年,她面对父亲薛事的离开,二十岁那年,她面对母亲娇贵的离开。这导致二十一岁那年,面对皓仲的离开时,她已经显得有些麻木。
娇贵将毛衣递给看守狱警时,都会留下一封信,这是十年来她一直坚持做的事。每当她看着漆黑铁皮门吞掉身后的风景,便像是合上了一整片记忆,已经有整整十年,她没有见过薛事,他躲着,躲在戒备森严的高墙里,如绝世老人般想方设法地终尽残生。
她想象过他如今的生活,只一方天地间。
十年前,薛事将整张脸埋在掌心里,瘫软在被告席上抑制不住颤抖的模样,娇贵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是一桩可能每年都会发生的奸幼案,却只在于事主亲生父女的关系,便轻易引起整座城市的轰动。流言如网。
这张网是一夜间铺开的,从邻里到大街小巷,漫天卷地。
薛事趴在病房门口的窗玻璃上最后看了岂容一眼,在安定剂的抚慰下,她睡得很沉。薛事给娇贵打了个电话,机械地报了医院和病房号,便硬生生地挂断电话。他双手冰凉的,一路僵疯着身体小跑,跑累了坐到路边花坛上抽一支烟,耳旁又响起了女儿的哭叫声,像尖刀划破玻璃的哭叫声。他心颤起来,鼻梁里还留有些许酒精的气味,冲进脑门,搜索般地追杀理智。他想骗自己,刚才那个沉睡的姑娘是娇贵,十几年前还年轻着的娇贵。只是那年的娇贵比起她要丰腴些,也是一双娇媚的桃花眼,眉梢隐处,也有一颗痣。
有人说,在这个面相上留痣的女人,一生风韵不断。所以,那是一颗桃花痣。
他跑进警局,众目睽睽之下有装疯卖傻的嫌疑,大叫,我是牲畜,我是牲畜!手指里还夹有小半支烟,一直烧到过滤嘴发出焦煳味;或许,那还烧到了他的手指,熏黑了一整片皮肤。等到警察们弄清楚状况记录备案,收押,娇贵才像头疯了的母狮一路冲来,她只问,我男人呢?
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夫妻。
所以流言交错了排开,如网密织盖起来。
很多人都说,薛事是在装疯,刑事医检下来,他一切正常。只是不说话了,不承认自己结过婚,有过女儿,还曾经是个诗人,打死都不承认;有的时候,干脆连他是薛事都一并唾弃,他说我是牲畜,你看不出来么?
宣判那天,他看娇贵和岂言的眼神很平静,她们像是所有前来旁听者其中的一员,融得很深,根本区分不开。他把肩膀垮下来,拒绝说任何话自辩,也不要辩护律师,只把脸埋在手掌里,只为了抑制住身体的颤抖。虚汗是从每个毛细孔里渗出来的,挂在耳垂上,挂在汗毛尖。那是格外安静的庭席,没有预想中的嘈杂和唾骂,所有人只是来看一个结果,像是为收起那张网做最后的总结。
诗人酒醉兽性大发。
强奸未成年亲生女。
这是第二天报纸社会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岂容的名字用“蓉蓉”替代那一年,岂言刚考入乘务学校,怀了几万英尺飞翔的梦嚷着叫着开始了寄宿生活,可这却成为岂容一场梦魇的开始。
这个梦魇对岂容而言来得毫无征兆,却留下了致命的伤。她从床上惊恐万分地翻滚下地板时,后脑磕碎了案头的一只水晶笔筒,血流了一地,和床上那块白色毛巾上的处子印记一起,像一场春天里绚烂开放的艳桃,薛事赤裸着下半身瞪大了眼睛错愕地看着。那种场面有些晦暗而情色,以至于十年里几次三番他又在梦中与之相见时,仍不住地心慌——酒精、血腥、干燥的木地板气味、窗帘、春天的阳光、背叛、恨、爱等等这一切交杂在一起,令他心慌,根本无法呼吸。他不敢低头看自己的身体,不敢拉开窗帘,风却轻撩地吹掀开一角投来光线,那时候地板上的岂容看上去像是一具久泡了福尔马林的尸体,头发散成扇形,皮肤上掠过窗帘花纹的影子,暗香浮动着。
那是第一次,他看到发育完毕的岂容,而她是那么白。
除了梦之外,十年高墙里的薛事没有记忆和过去。他总在纸上记录今天的心愿,始终只有两个字:猝死。
岂言靠在床边等西蒙的时候发了一个梦。她听见母亲娇贵小时候经常会唱的那首儿歌:
船渡儿,月牙儿,囡囡小手捧张儿。
日日长,夜夜长,妈妈心坎花房长。
儿歌是父亲薛事随口说的,他喜笑颜开地抱着蜡烛包里的岂言,就这么哼出来。那是腊月的冬天,四周一切都是白色的,医院阴冷的空气被消毒水淫浸湿透。岂言记起父亲的脸,惨白的,露出两三条抬头纹,笑起来的时候唇线可以延伸得很远,他的手巨大,却滑净得没有一只老茧。小时候,父亲总是伸出手来抓起岂言的手腕走在街上,她喜欢问:“爸爸,为什么你不抓我的手呢?”
薛事听见就笑,边走边说:“现在言言的手太小,爸爸怕抓不住;等你长大了,手是要交给心爱的男人抓的。懂吗?”
这样的话,在其他家庭,应该是母亲对女儿说的。可在薛家,从小,岂言就是紧贴父亲长大的。因为母亲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岂容,她的小女儿。
已经整整十年,岂言没有见过父亲。刚开始的时候,她坐等在探监室里一整天又一整天,一直到宿监来赶人才离开。她把眼睛哭得像两枚新鲜的胡桃,肿出细小水泡来蔓布眼眶,那年她才十六岁,刚刚萌生了丁点的情爱之心,只是这种野草般的骚动,是向着父亲肆长的,她自己也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渴望他的毛糙短胡子刺过自己的身体,然后紧紧拥住,紧紧拥住。
虽然除了母亲娇贵的手之外,父亲从不抓别人的手,包括她,包括岂容。
可就连岂言自己也分不清对于母亲娇贵的疏远,究竟是埋怨了那一巴掌,还是根本就是嫉妒。嫉妒母亲有丰腴的身体,白皙的皮肤;嫉妒她总穿了花卷腿的半截睡裤露出藕嫩小腿,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嫉妒汗水一旦在夏天湿透了她的真丝内衣,就会隐现出可怕的曲线,那是连小女孩看了都会心神漾然的曲线。母亲像是从老上海月份牌里雕琢下来的慈悦女子,笑起来眉眼都是弯的,风韵得很。
那时候岂言固执地认为,这种风韵是自己一辈子都得不来的。
所以,当她在诊所里发现了母亲频繁看牙医的秘密后,嫉妒就如同初夏风仙花饱和的花子儿盒,轻轻一捏就爆开了芯,秘密撒落一地。她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偏喜欢带着岂容同进同出,偏喜欢在那个盐碱味密布的夏天一周看两次牙医了。都明白了,包括妹妹岂容为什么总在夜里睡不着觉,为什么总说自己的脑袋冰凉。
岂言透过那一幕帷的帘子,看见了母亲娇贵,看见了阮姓牙医。白瘦的岂容睡翻在外屋的沙发上,面前是一小杯橘子汁。十八寸彩电里播放着《新白娘子传奇》,白素贞和各种神仙打得难舍难分。那间诊所里的气味如同一枚枚银针直刺人脑皮层,它们扎入得很深,令她头皮发麻,各种声响交错在一起迎面轰来。岂言缩在墙角根,屋内屋外的风扇一遍遍吹起门帘,母亲娇贵赤裸在那张黑色皮椅上,看起来,是那么白,那么白。
岂言记得那样的气味,夏日江水盐碱里的咸,消毒水的冰腥,汗水的温潮,还有芬达橘子水的腻甜。她感觉到自己下身的同时燥热,感觉到从耳根蔓延到脸颊的灼红,那是从心里烧起来的火。第一次,她觉察到自己身体里有欲望的存在,那年,她才十五岁,初三。
阮姓牙医的身体是麦芽色的,肩膀张开,后背露出明显的线条,那不是肌肉打下的线条,而只是汗水,它们顺着皮肤歪歪扭扭地滚下来,涂鸦出一片。他的臀部收得很紧,猛烈来回撞向椅子上白若雕塑的娇贵,阳光从他们面前的窗口射进来,在尘埃里化作一片妄孽的明亮,如噩梦惊醒般。
供病人仰躺着治疗的黑色皮椅一侧停着牙科仪器,奶白的漆色,地下候着一只小小的漱口水杯子。杯子在剧烈的晃动中不停地变换位置,跟随娇贵起伏的呻吟声溢出来,收回去,再溢出来,再收回去。岂言后来几乎把目光都停留在了那只小漱口水杯子上,她觉得自己的确需要一丁点水来浇灭泛滥起来的火,因为它们正随着早已疯长盼情欲野草围剿蔓延。
当麦芽色的身体力竭而俯上娇贵时,她湿透的额头微微皱起来,眼神从迷离到清醒,再到不可抑制的惊恐,门帘吹起一角来,光线不明的走廊上,是一个女孩的阴影。第一秒钟的时候,娇贵以为是岂容,她推开已经瘫软在身上的阮一骞,伸手去抓落在地上的连衣裙,一次没有抓到,两次还是没有抓到,第三次,她低头去找的时候,从门帘里看到了岂言的深红色塑料凉鞋,它们飞快地移动,然后消失。
娇贵用连衣裙盖住自己的身体,后脑勺重重地砸向黑色皮椅,断了自己的呼吸,只轻声说了一句:天哪。
《上海往事》播了好一会儿,终于结束。娇贵将毛线放回篮篓里,站起身来去阳台上抽卷烟。十年里,她给薛事织过十二件毛衣,手上的这件编号13。她记不得自己写过的那些翻墙入狱的信件内容了,甚至有几封根本可能是空白的。她总是记不住一些事情,重要的,不重要的。有时候,娇贵难得清醒,便会突然神经质地将自己后来的三十年的记忆重新犁一遍,可往往越到后来,这种回忆就越像一场刑役,她在亲手用钉耙将自己犁得遍体鳞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