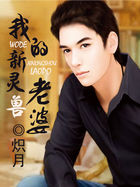这一年全校毕业生总共一千余人,公开被定为反动学生的只有我一个(听说仅中文系每班还有内定反动学生2名,全系共8人)。平常在学校里默默无闻,这一次真是臭名远扬了。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全国的政治运动有五六十次之多(有兴趣的可参见我的《说运动》一文,连载于《社会学茶座》2007年1-5期),许多运动有时也烧到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但专门以大学生为清理目标的只有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清理反动学生运动。被清理出来之后,不算合格毕业生,不能毕业,分四等处理。一、劳动教养三年;二、劳动教养二年;三、劳动考察三年;四、劳动考察二年。我是劳动考察三年,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农场劳动。因为“文革”拖到一九六九年初才又回到学校,一九七一年分配到房山。
第三次最为严重,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初。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文革”虽未结束,但政治环境稍显宽松。因为自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出事以后,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感觉到没有从流行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往常的激烈的信仰,日益流失,人们平静下来后,更加感到往日的荒唐。虽然,每个人到了单位依旧是粉墨登场,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但私下里,却敢于悄悄地说些真话了,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我们这些普通人一天二十四小时、无论对谁、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说瞎话,心理上是承受不了的。真是“一个人说点假话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说假话,不说真话,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也许只有大人物才能做到像邵燕祥先生所说的“口吐铅字”,永无真情实感,而普通人是绝对做不到的。
大约到了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人们心理承受度已经达到极限,又没有正当的发泄渠道,于是以前的腹诽变成了现实的言语,有流言、有非议、有小道消息、也有谩骂诽谤(正是这种情绪酝酿了后来的“四五”)。即使最胆小的人,有时忍不住也要骂一下社会上的极端表现(当时视为革命行动),只不过最后还要加上一句“这些极‘左’的都是林彪那些人搞的”。
好像这就安全了。当然,我也不免俗例外,因为都是普通人,就难免会做一些面上毫无表情、私下里叽叽喳喳——不合君子规范的俗事。我最反感的是“批林批孔”,连震撼千古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都能改成“小丑一去兮不复还”,夫复何言!更可笑的是,当时批判什么都能挂在孔子的账上。如批“走后门”就联系“子见南子”;批“男尊女卑”联系“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批“英雄史观”联系“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批“复辟倒退”联系“觚不觚,觚哉觚哉”,可笑之至,可耻之至!
一九七四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指出“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当一九七三年除夕夜听到这篇社论的广播时,便预感到风向要变,要更加极端了。果然不久就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但这次的极端,很少有下面的群众响应了。从上面的极端主义的言语作风看(例如要搞“全面专政”等),好像有点像要重新点燃群众的革命激情,回到一九六六年去。然而一九七二年以来,民间的不满、各种议论和传播小道消息却渐渐形成一种惯性,不能停止。上面视为这是资产阶级全面进攻,不断地增加打击力度,并时时以“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路线斗争新动向”告诫下层领导。
而且各部门、各地区也在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打击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当然北京也不例外。一个纯属偶然机会,我被牵连出来了。这次事故最大,被列为打击对象,没有经过群众运动,一步便到了专政机关。先是被房山县公安局传讯,再是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之后,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运动覆盖中国大地之时,五月十日我再次被升级,被逮捕,由北京市“中法”提审。于七月二十六日,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平反后,听我弟弟说,你的案子拿出来交群众讨论了,他的一个朋友在友谊宾馆工作的看到过。那时凡是“交给群众讨论”的案子,都有几分凶多吉少。我的案子经过这讨论,应该是众所周知了。不过除了原先就认识我的人,光凭“讨论材料”
中的所着录的“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谁也不会因为这些空洞的罪行记住王某的。因为在大批判中、在“清队”中、在“一打三反”中,乃至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听惯了这种指责,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对待的。我工作所在的房山也惊讶出了一个判处十三年的“现行反革命”,从我判刑的七月二十六日起就准备召开全县批斗大会,不过这个会,命运多舛。
先是七月二十八日大地震,大家抗震,顺序后延。后定在九月十日召开,不料,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紧跟着“四人帮”倒台,于是,批斗我的全县大会也就不了了之了。
记得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幸亏划了右派,要不,我本来就平淡的一生就更加平淡啦。”汪先生生在高邮,经过抗日、辗转大西南,跑过日本空袭警报,进入了“西南联大”,受过一些前辈大师的亲炙,跟着沈从文先生学写小说,后来又写样板戏《沙家浜》,至今传唱不衰,小说更是别具一格。他尚如此说,至于像我这类一九六○年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受的是驯服工具论的教育,又欣逢不许读书的年代,用李泽厚先生一九七九年在《鲁迅思想分期》一文中的话说是属于“长期在外力和内心压力下,知识少而忏悔多”的一代,与汪曾祺等前辈相比只能更加平庸,更没有谈谈过往资本。“幸亏”有了这三次挨整,见过了许多世面,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之事,也见到了一些难得一见之人,也就是“怪人”①。这还是同辈人中经历中不多见的,有时说起来,如同“进了几回城”的阿Q、可以夸示于未庄的小D、王胡一样,也不免堕入“津津乐道的恶趣”。然而,我有一点是真诚的,就是希望后辈别再有这样的经历,中国再别发生这一类的故事。
我的第一个“监狱”
这个题目中的“监狱”只是一般用法,是指政府关人的地方,并非是法律文书中的监狱。一般外人(指没有进过监狱的、又非公安人员)把政府关人的地方都称之为“监狱”,而在法律文书中,其间区别很大。通常的就有收容站(据说现在已经取消)、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包括监狱工厂、监狱农场。监狱农场老百姓一般称之为“劳改场”。
收容站是收容盲流的(改革开放前,人口不准私自流动,凡私自流动者就称之为“盲流”,警察见到就要送往收容站),包括许多上访人员和无业游民,有时候也关一些找不到理由关他、但又非关不可的人。那时从理论上说这些人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北京的收容站设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人们简称为“功德林”。这里因为是临时关押、流动性大、经费少、收容量大(特别在节庆或有重要外宾来访期间),伙食特别差。一九七○年代中,北京看守所、监狱的伙食费已经是每月十二元五角,功德林才六元,就这样有的到北京上访的也愿意去。我遇到过一个从功德林转来犯人,他说,有天晚上,快熄灯了,有个三四十岁胖女人,听说是通州上访的。抱着一个孩子,拖着两个孩子,非要进来,看守拦住、并轰她走:“去去去,你怎么又来了,这没有你的地方了,又跑到这里吃白饭了!”女人边闯边理直气壮地说:
“谁稀罕你们那两个破窝头,这么晚了,我到哪儿睡去?不到你们这里,到哪去?”说着就拖着孩子往里走,看守也无可奈何。
因为被关的人从道理上讲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功德林不上锁,只是把门从外面插上。据说功德林是模仿八卦盖的,关押在这里,开着门也很难跑出去。
拘留所在一九七○年代属于北京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管,它关押的大多是违反治安条例的。行政拘留的处罚,也在这里执行。那时行政拘留最长是十五天,这些人进了拘留所,大多是几天十几天也就放了。少数被公安局“判”(书面语言是“送”)“强劳”(强制劳动,比劳教轻)或“劳教”。一些案情复杂、一时弄不清的嫌犯,那时也采取拘留处理,有以拘代押,以拘代审的。如果被逮捕了(签署了逮捕证)就要升级到看守所了。北京市拘留所在东城炮局胡同,简称炮局。拘留所的人员流动仅次于收容站,这里伙食也不行,一些常常出入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小青年们有顺口溜有云:“富宣武(宣武公安分局监押机构的伙食较好),穷朝阳,炮局窝头眼(儿)朝上。”
“看守所”本来应该关押逮捕以后待审人员,但“文革”期间以拘代押,以拘代审的人大多也是关在这里。它在普通百姓中是个陌生的词,我曾听一个初次犯罪的中年农民说:“我从看守所门口过,见有当兵的拿枪站岗,以为是看守国家财宝的地方呢!这回才知道是关犯人的监狱。”
大多数人称看守所为监狱,这是不确切的,它也只是个临时看押机构。到看守所来的犯人,大多是被逮捕起诉了,在这里等待正式审判和判决。正常的法治社会,看守所一般关押的是被起诉的、但有可能逃逸、串供、继续犯罪、或对证人有威胁的嫌疑犯罪人员(如目前陈水扁就是因为有可能“对证人构成威胁”,才被收拘的,否则,在特侦组调查完毕、起诉后就可以在家中静候法院传票了)。如果嫌犯没有这些可能,一般是在家中静候法院审判。被法院判有罪,则进监狱。
一九七○年代我们是公开说不搞“法治”的,不用说被起诉的人员了,只要一被怀疑有罪就有可能被关押。为什么三十年前,平反了那么多的冤假错案,甚至可以说是“囹圄为之一空”,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一套健全的法律制度,一切都是政策和领导人说了算,不仅打击面过宽,而且株连了许多无辜的人,甚至可以说是“冤狱遍于国中”。
上面说的仅仅是北京市一级的情况,市以下的八区九县,各个区县都有公安分局,每个分局都有监押机构,但不可能像北京市分得这么清楚了。
一九七五年三月四日,我在县文教局被隔离三四天后,被送入了房山县公安局,说是“传讯”。传讯按说比拘留还轻着一级,现在简单传讯,大约都是在派出所问一问,更客气一点叫到饭馆(真是应了“革命从不是请客吃饭,到革命就是请客吃饭”这句民谚)、茶馆、咖啡馆,聊一聊,警告一下,俗称“请喝茶”或“请喝咖啡”;时间长的,关到宾馆等。这是政府有钱的表征。那时,正经为公家出差还没有宾馆住呢!
我被传讯时,房山县公安分局的拘留所、看守所合为一体。这两所与县公安局在一个院里,它们被有电网设施的高墙圈出,四个犄角有炮楼似建筑,上有当兵的守卫。候讯室是在它之外盖了两间平房,表示此处与拘留、逮捕有别。这两间房子不上锁(从外面反插着),里面还有火炉(因为是进去时是3月15日之前,按照北京的取暖规定,此时还有火),用以表示这里是收容和候讯,不同于拘留、看守和监狱,然而,它比前三者更糟。
因为是收容,里面关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者,如流浪的精神病患者、痴呆者等。又因为在这里的多是短暂关押,没有人为之清理、清洁。我一进入这间屋子,第一感觉是一股难以形容的恶味,是臭?
是腥?是臊?说不清楚,外面闻不到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我只感到要呕吐。我一进屋,对面几个小鬼似的人吃惊地从炕上(实际就是半尺高的光板炕箱)爬起来望着我。这就是我进的第一个“监狱”,在此之前虽然也倒过许多霉,但监狱还没来过,这次又添了新的阅历。它给我留的印象极深。
最引人瞩目的是个坐在室内中心地上的大头、细脖、消瘦、眼大无神、头发齐肩、穿着肮脏的青年人。这人对外界反应很小,我一坐定,马上有些人把他推开,“疯子,你一边去!”争着围在我这个新进来的人身边。“你什么事?”这几乎是千古不变的老问题,新入监的犯人一进入号子,就会遇到这类的提问。
我感到为难,怎么说呢?“……就几句话,大约是政治问题罢?”“嘻……”周围的老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了。“这屋子还没来过这样的人呢!”大家又笑了。“你们倒高兴?”我有些生气了。有个青年工人把脸伸向我说:“师傅(那时的官称),您看看我眼睛还红着哩,有什么高兴的?大家是看着您新奇。”我说:“这有什么新奇的,现在这类事挺多的。你什么事呢?”青工马上一脸愁苦说:“我是琉璃河水泥厂的电工(这在当时是很体面的工作),新结婚,到“东炼”(东方红炼油厂的简称,即现在的燕山石油化工厂)来换两身军服,被“东炼”保卫处扣了,说我有意诈骗(那时青年人以军装为时尚服装,换来换去的很多),我有个本家哥哥就在房山分局。”他大约没有说谎,整个候讯室就他有床被子,是局里借的。一般传讯是不借给被子的。
我环顾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四壁黢黑,大约是烟熏的,因为每天都在室内生火。墙上屋角挂满了蛛丝和尘灰,地下一个犄角堆着二尺高的麦秸,这是给睡在地下的人准备的。新进来的人,由老号看一下他是否有资格睡在木头炕箱上(主要是脏不脏),没资格就让他垫着麦秸睡在地上。即使监狱也是有等级的。那个疯子就睡在地上。
一会就和这些老号混熟了。他们主动向我诉说他们的案情,让我帮他们拿拿主意。睡在我旁边的一个姓谭的,对我说,他是三六○八厂的,一天他去房山县城买东西,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抓住他说,某天谭在大石河搂抱她、亲嘴。谭说那天我正在上班,不可能去大石河。这应该是很容易弄清的问题,不知为什么,这个谭某被关了二十多天了。我对他说,这很容易证明的,让你们单位的领导或同事出具一份那天你在上班的证明就可以了。
另外,有两三个河北老乡,他们有的是到房山收购破铜烂铁,有的是联系买煤(房山许多公社出煤),都被以投机倒把罪抓进来了。其中有一个四十来岁程姓农民一副要哭的样子,对我说:“您看看,不就因为在房山有个亲戚,联系点煤。我们那里是有吃的,没烧的,这里是有烧的,没吃的。我给联系联系,换一下,挣点辛苦的跑脚钱,这就叫投机倒把?腊月二十七那天,被抓进来的,一关二十多天了,媳妇包好了饺子等着我过年,孩子也等我赚俩钱买炮仗呢!”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旁边一个三十来岁有点监狱油子样子的人厌烦地说:“别说了,怪讨厌的。身子掉到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先想想你怎么应付预审员罢。”
这个油子样的人实际上才二十四岁。他十八岁那年被判过一次。这屋里就他不发愁,该吃就吃,没事就睡。还受到一些室内“玩闹”(文革中后期,一些胡同串子,小打小闹,小偷小摸的小角色称之为“玩闹”)的崇拜。当有的“玩闹”对他不够尊敬时,他会横起眼来训斥他们:“你们算个屁。见过什么?五处(北京公安局劳改处又称“五处”)你去过吗?大镣你趟过吗?万人批斗大会你撅过吗?”于是小“玩闹”们只得低头服软。
我问,因为什么那么年轻就被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