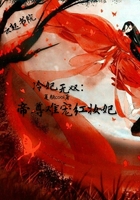此时,月夜之下,一尊孤影伫立,稍显落寞。夜无眠,本是想漫步于庭中,但奈何空庭太过清寂,本为草莽少年的他又缺乏高雅之趣,既吟不得诗,也作不了对,只得在夜下静立,瞧着那如霜地面上自个儿的孤影,怔了良久,方才拔出手中之剑,于月下挥剑起舞。
庭中幽寂,唯听剑声呼啸;月色皎白,但见光影幽闪;风过竹梢,拂起衣袂飘扬。自入宫以来,压抑天性的他,许久未曾这般痛快过了,那积压已久之绪,在这舞剑之际,发泄的酣畅淋漓。一舞作罢,他方收剑稍歇片刻,平息之时,忽闻庭中假山后传来窸窣之声,便抬眸望去,只见其间有一人影闪过,心下惊觉,便赶忙提剑奔了过去。
“是谁在那儿?”
他抬声问道,等了良久,见无人回应,便一剑刺了过去。
“啊——”
霎时,假山后传来一女子的惊呼声,慕容昌胤听罢,心中猛然一惊,赶忙翻身至假山后探个究竟,立于此时,却见一个女子猛然于草丛中起身,借着明亮的月色,方瞧见那女子神色惶恐,一副受到惊吓之状,此刻,那双犀利的眼眸正防备的盯着自个儿。
“姑娘没事吧?”唯恐自个儿伤到人,慕容昌胤赶忙问道。
“能没事吗?”只听那女子反问道,“我正于庭中侍弄花草,忽然一把剑刺了过来,吓得我魂儿都没了,还好躲得快,要不然,可就得死于你的剑下。”
面对这女子的埋怨,本就不善于与女子调笑的慕容昌胤神色冷峻,再加上年少轻狂桀骜不羁的性子,更是不愿低头赔不是,遂,只得侧眸转身,道:“还是这般的伶牙俐齿,看来那一剑,定是无碍。”
见少年那傲慢之状,女子微有薄怒,便扔下手中所携的锄头,挡于他的面前,正声道:“你这人当真是无礼,险些误伤了人,难道不应低头赔个不是吗?”
少年横眉迎上她的目光,缓声道:“你于三更半夜间,藏在假山后的草丛里鬼鬼祟祟,行迹着实可疑,我本东寒宫侍卫,职责所在,过来瞧瞧也无可厚非,何况事先还抬声问候过一句,奈何无人回应,遂才举剑,若是有错,也是你犯错在先。”
“谬论。”那女子反驳道,她眼珠沉静,于夜色下瞧着少年,“我乃东寒宫新来的宫女,专掌花草侍弄修剪之务,近来外头甚热,不得出门,念在夜间凉快了些,便出来庭中为花草剪枝,本是念在深夜庭中无人,忽闻人声,尚未回过神来,却只见眼前寒光一闪,一把剑便刺了过来,还好我闪得快,未伤着已是万幸,你竟还怪罪于我?这是何道理?”
“此事,你我二人皆有错,如此再争论下去也是无意,不如就此作罢。”
言罢,慕容昌胤无心再与她争辩,便独自转身,正欲离去,却听身后又传来了她的声音:“明知自个儿错了却想尿遁,此非君子所为也。”
此言,带着叹息和讽刺,本就心绪怅然的他也无心计较,只单抬步,于夜下出了空庭。此时,独立于原地的董萼望着那折身离去的身影,而后,收回眸光,继续俯身蹲于花丛之中独自忙活。
回到房中的慕容昌胤逐渐平复了心绪,方将手中之剑扔至一侧,和衣卧于榻上,暗想着年少朦胧的心事,星眸直直的怔望着夜色发呆,撑到凌晨,方才浅浅睡去。少顷,夜尽天明,晨钟响起,那宫中一片哗然,微有聒噪。少年睁开眼眸,从榻上起身,洗漱之后方携了床头的剑,快步往庭中奔去。
外头的宫道上,早起的宫人皆匆忙行于各处,东寒宫内,因时辰还早,尚不见人影。此时,空庭宁寂,晨风清凉,让人倍感舒爽,立于此间的慕容昌胤方除去剑鞘,挥剑舞于庭中,毫无拘束,甚为畅快淋漓。
此时,从寝殿走出来的高越瞧着那个于庭中舞剑的少年,眉宇舒淡,眸色悠然,方缓步下了殿阶,往庭中走去。
那舞剑的少年闻见了脚步声,眉头轻轻一挑,闪现薄怒之意,方转身,挥剑朝那下入庭中之人刺去。下一瞬,越神色如常,毫不半分惊恐之意,仍旧淡看着眼前举剑对着自个儿的少年,只见他却横眉冷对,向来桀骜不逊的眼底此刻暗含着愤懑。
两人对峙,良久,越轻抬手中折扇,挡去那刺于面前的利剑,而后,冲他微微一笑,悠声道:“清晨舞剑,慕容公子当真是好兴致。”
言罢,他便绕过那少年往庭中走去,坐于石案之上,独自品茗。慕容昌胤见他一副悠然骄矜之状,心中更是不满,便收剑,瞧着他的背影道:“听闻高越太子文武双全,剑术更是不在话下,今日得闲,不如你我二人切磋一番,如何?”
听闻此话,越放下茶盅,悠声道:“咱们二人切磋,赢有何意,输又有何意?大好的男儿,若将一门心思放在争强斗狠之上,着实难成大器,得闲之时,不如静坐品茗,也好沉淀沉淀那桀骜的气性。”
“怎么?殿下竟然不肯?”那少年再次举剑于前,冷声道。
越抬眸,迎上那少年的目光,应声道:“不是不肯,只是不屑于此,我乃大燕太子,心系天下,断不会为此等琐碎之事计较。”
“大胆——”
话音刚落,忽闻庭前传来一女子的呵斥之声,高越闻声抬眸,只见玉菡携侍女匆忙下入殿中,挡在他的面前,冲那举剑的少年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剑指着殿下。”
“玉菡。”越起身,神色如常道:“清晨之初,庭中宁寂,让人颇感惬意,遂,慕容公子便想邀我一同舞剑,也好切磋切磋剑术,仅此而已,你错怪他了。”
听了此话,玉菡神色渐缓,一改方才的急厉之色,冲那少年清淡一笑,微微俯身道:“方才是玉菡鲁莽,未弄清缘由,错怪了慕容公子,还望公子见谅。”
他一副云淡风轻之态,仅寥寥数语,便轻易化解了一场矛盾。立于原地的慕容昌胤不禁暗叹起眼前这个男子的城府之深,虽心中恼怒,但也别无他法,最终只得愤然转身离去。
此时,玉菡抬眸,瞧着那少年愤然离去的身影,心中甚是不解,越有所觉察,便垂眸冲她微微一笑,转话道:“你今日为何起的这样早?”
“听说长桥湖里的荷花开得甚好,玉菡一直想去瞧瞧,奈何近来天气甚热,不宜出门,遂,便于今日起了个大早,想趁着初晨凉快之际去桥上走走。”玉菡笑着应声道。
“如此甚好,你且去,于日出之前快些回来便是,免得热坏了。”
听了他的叮嘱,玉菡心中甚喜,冲他点了点头,正欲离去之时,方又回过头,瞧着他,道:“解暑汤已经吩咐宫人熬下了,待正午之时,会给各宫送去,近来接连几日给各宫送此汤,众位嫔妃宫人皆喝过,且都对殿下此举赞不绝口。”
“有劳你了。”
越随声应道,待玉菡离去,那抹淡笑方才逐渐止于唇角。
那日,他端着羹汤,缓步走进燕平宫,守在外头的夏邑瞧见了,便赶忙迎了过来,道:“太子殿下,您来的可真不巧,大王这会儿正在殿中睡着呢。”
“现下还未到晌午时分,父王也还未用午膳,怎的就睡下了?”他低声问道。
“奴才也不知,许是入夏以来外头闷热,人易困乏,易睡倒也不足为奇。”
“那倒也是,父王一直都为国事操劳,能暂歇片刻也好。”言罢,他举了举手中所执的羹汤,遂又道:“我来给父王送羹汤,这汤原是润肺止咳之用,凉了再喝效果更好,现下父王既睡着,我便进去瞧一眼,将羹汤放下便走。”
“殿下,您请吧。”
夏禹抬手道。越听罢,便命身后的尚子等候在此,而后独自一人缓步往殿中走去。大殿唯有玉漏之声,宁寂无比,不沾丝毫人气,他瞧见了独坐于侧榻扶额小憩的燕王。那昔日高大清孤的帝王,于这幽暗清冷的大殿之中,愕然浅睡的模样,显得苍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