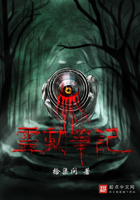寝室长出狱的时候对我说“所有过往的经历都不能构成你堕落的理由,你得好好活着”。如今她安然地躺在这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被人遗忘,被人追忆,她为自己找了千千万万个死去的理由。
决定了要离去,就会滋生无数个理由,这依旧取决于自己的需求。
这些日子我总是对着墙壁发呆,笔记本上满满的写上了我对未来的遐想,我依旧没有放弃对未来的追求。时光一闪我发现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想吸的欲望了,我正在慢慢的跟过去的自己告别,或许前面的路布满荆轲,我永远都不想再回到这个铁笼子,身上的伤口慢慢愈合,变成时光的印记。
诚诚总是问我:“我的妈妈去哪儿了,她什么时候才回来看我”。
“快了,快了...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就会回来”。
我摸着他的头,像是抚摸着我当初失去的孩子。
“肖妈妈,你快点出来哦,我要开家长会了,明年还要竞选班长呢”。
“嗯,我努力。”
我爱他,可是我却不曾这样爱过自己的孩子。
面对他,我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跟他讲明真相,他需要一个幻想,如同李妈妈思念自己的女儿一样。
我不能保证将来知道真相的诚诚会有怎样的翻江倒海,只能尽最大努力把痛苦降到最低,用我全部的爱来弥补这三个人之间战争带给孩子的伤痛。
苏眉永远走了,再也没有消息。李妈妈也再没收到包裹,我托小琪给她寄送了冬天穿的衣物,她也需要这种幻想。
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流淌着润润的河水,可是已经发乌,发黑。每到夜幕降临,这潺潺的流水声像是一头发情的猫在细细叫着。
姑娘们踩着高跷,露出雪白的大腿,男人们勾肩搭背,冒出污言秽语。下班族手提着空荡的饭盒簇拥在密集的地铁口,男男女女聚拢在一起谈论谁家的变态经理又开始折磨谁了。
一切都还在上演,生活还在继续。
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华哥应该穿着反光的皮鞋,用高档的摩斯盖住自己的“地中海”,屁颠屁颠的招呼着客人,他的眼里满是白花花的票子,只有一张张票子才能填补他作为一个“废人”的空虚感。
我说,我永远不会再回到华舞汇。
他说,他离不开华舞汇,那是他的家。
我们注定只是生命中的旅人,谁又不是呢。
“华哥,你不觉得亏欠吗。”
“我为什么要亏欠,肖林,我从来没有逼过任何一个姑娘,都是她们自愿的。”
“你想过以后吗,你不想有个安稳的家吗。”
“想,可是世间万物,不是想就能得到的。那要付出代价,我付不起,我就守着华舞汇,离开这里,我什么都不是”。
刺耳的音乐在夜幕到来之际变得更加有力,舞池的姑娘换了一个又一个,那些烂醉如泥的“哥哥”们也换了一批又一批,永远不变的是华哥,那个自卑而又自尊的男人。
寒来暑往,谁又留下,谁又离开。
“李妈妈,最近生意好吗”,我好像都能背出她的电话号码。
“挺好啊,我都快半年没有看到你了,在忙什么啊”,她的声音里透着愉悦的气息,看样子今天生意应该不错。
“忙生意呢......李妈妈,您的女儿找到了吗。”
“应该找到了吧,她还是不愿意见我,不过经常寄东西,我想她过得应该不错。等我老得快死那天她要是还不愿意见我,我就把存的钱都给你了,你帮我买口棺材就行”。她傻傻地笑着,好像等待成了她生命中唯一要做的事,高兴或悲伤,只有自己才知道。
“李妈妈,可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小娇很关心您,她不愿意见您,或许有些苦衷吧。”
她岔开了话题,咯咯地笑了两声。“等你哦,等你忙完了来我家吃饭,我给你做糖醋鱼”。
挂完电话后我感觉异常的开心,冬日的暖阳爬上了树梢,一阵清风打在玻璃窗上,原来季节也是有生命的,我度过了三十多个寒来暑往却没有发觉季节的变迁。我一无所有,我是一个从窑洞里捡来的姑娘,没有了父母,没有了兄弟姐妹,只有一副半残的躯体。
可是我感恩时间,让我学会了感受疼痛和开心。我感受到了李妈妈的等待,感受到陈少南的迷茫,这一切都是自然规律,谁也不知道脚下是深渊还是平原。我开始慢慢往这副没有灵魂的躯体塞进一些情绪,让她温暖,让她害怕,让她渴望。我开始学着害怕疼痛,不敢用开水烫自己的身体,学着走出宿舍大门,跟室友们聊聊天,聊一聊哪个女人今天又偷情了,谁又跟谁睡了。
我哭了,我竟然错失了那么多的过往,就算命中注定,我也应该享受所有的喜怒哀乐。
我活在一个自以为可以拯救家人,拯救朋友的虚幻世界,我以为卖掉了自己就可以换来家人的幸福,父亲的健康。今天我才明白,肖林,你真的没有那么伟大。
哪里才是家,有心的地方便是家。我迷失了这么多年,找了这么多年,终于肯沉淀下来了。
“妈”。
叫出这个字后我和她一度陷入了沉默,那不是尴尬的沉默,而是岁月腐蚀掉的默契。
那天她穿着棕色的羽绒服,细纹粘贴在眼角上多了几分慈祥的样子,我坐在她的面前却忐忑不安。她再也不是那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女人,精修的眉毛勾勒出城市人的时尚,可我对她的记忆还保留在那个偏僻的小从村,那年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踩着一双破旧的黄胶鞋在地里挖红薯,嗡嗡的蚊虫在夜幕中高歌,她扛着锄头回家生火做饭。
我的心难受之极,我爱着那个蓬头垢面严厉的母亲,心疼她在工地上捡砖散瓦,当年她离开的时候,黄褐斑在脸上散布成一个三角形,活像是一只晒熟了的猴子。如今她脱胎换骨,我好似错过了几个世纪。面对时间流逝,我们是这么的无能为力却又兴奋不已。
我们坐在各自的对面,打量着对方。
我的母亲,原来就是那个悄悄来看我的卷发女人。
我没有哭,她也没有。
“活了大半辈子,熬了大半辈子,还是回到原点,其实我挺羡慕你父亲的。
”她的目光很满足,让人很难相信她过得不好。其实她过得挺好,就像我一样,一旦对疼痛失去了知觉,所有的神经也就麻木了,于是,疼痛变成了享受。
“他是得肝癌死的,天天陪客户喝酒把自己喝废了,给我留了一套房子和一笔存款,我也帮不了他什么,好好过日子吧。”
“嗯,对。”
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这或许就是她的心里话,她的目光温柔,很难看出经历过悲伤,这种岁月沉淀下来的东西我是感受不到的。
“我幸福过几十年,足够了。只是这世上,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她的声音开始变小,变弱,面对我,她说话没有了底气。
“你永远是我妈妈”。
我望着夐远的苍穹,空旷的天空时不时有几辆飞机闪过,我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人各有命,安心活着,这个道理我当初不懂。”
“肖林,回家吧,我和你的两个弟弟在等你”。
我的身体内上亿个细胞开始发酵,发出流泪的讯号,我憋住肿胀的瞳孔让眼泪倒回肚子里,可是我抵挡不住这强大的冲刺,它肆无忌惮流在我的脸上,脑袋里嗡嗡的,打乱了呼吸的节奏,开始抽搐起来。
“走!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