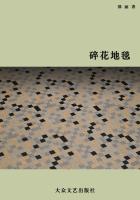四连所驻扎的学校旁是一片树林,穿过这片树林,是条公路,穿过这条公路再走两条街,就是一条妓女云集的小街巷了。这条街臭烘烘、滑腻腻的,到处都有油渍、纸屑、果皮和痰液。但这条街总是张灯结彩的,浮动在门楣上的漂亮灯饰掩饰了地上的肮脏。这条街的地面被第十军的官兵踏出了一个个坑,原来不大的坑在官兵们有力的军鞋下,拓宽了很多,那是大兵们的脚踩出来的。他们大踏步地在这条街上走着,高兴地跺着脚,吹着口哨,搂着姑娘,与姑娘亲吻或者让姑娘们坐到他们腿上。他们奉行及时行乐的政策。他们向姑娘们吹嘘说,他们誓与衡阳城共存亡,要她们不要怕,因为有他们保卫衡阳。
“那我们不走。”妓女们感动地回答。“不走就好,你们一走,这座城市就尽是男人了,”第十军的官兵说,“没有女人,男人活着也是白活。”妓女们可怜这些男人说:“好了,乖乖,我们会陪你们的。”第十军的官兵高兴了:“就冲你们,我们也要把衡阳守住。”妓女们高兴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就靠你们啦。”第十军的官兵非常自信道:“没问题,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
其实第十军的官兵心里都清楚不定哪一刻脑袋就搬了家,子弹、山炮、野炮和飞机扔下的炸弹都会叫他们丧生。他们害怕白白死去,所以他们要及时行乐。
“到时候,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尘世上的,你都不晓得呢。你不亏了吗,程眼镜?”钩鼻子开导程眼镜说,“去吧去吧,你至少也要去玩一次。”
“我不去,”程眼镜说,态度很坚决,“我是来打日本鬼子的。”“去吧,程眼镜,”毛领子既劝程眼镜,又劝童大嘴说,“走啰走啰,一起去散散心。”
童大嘴不屑于玩女人说:“你们去。我不去。”“我也不去,”程眼镜说,表情不容置疑,“我要对得起苏豆壳的妹妹。”“苏豆壳的妹妹是你的未婚妻?”毛领子问。
“不是。”程眼镜说。“那你要对得起她什么?”毛领子挖苦道,“你不是有神经病吧,你这人?”“不是神经病,而是为了爱情,”程眼镜一脸道德和神圣,不屑于去妓院找姑娘玩,“我这人你们不了解,我这人的毛病就是对爱情忠诚不二。”毛领子大笑:“还忠诚不三呢,我会笑死。”程眼镜等毛领子的笑声落下后,又急急表白道:“你们交我这样的朋友真是交对了,我这人是死脑筋,对朋友从来没有二心。”“我也不去。”童大嘴说,看一眼毛领子、钩鼻子和在一旁暗笑的谢娃娃。钩鼻子觉得童大嘴没有道理不去,问:“为什么?不是爱上了哪个姑娘吧?”
童大嘴一脸坚贞道:“我要对得起苏豆壳的妹妹。”“你也喜欢苏豆壳的妹妹?”程眼镜惊愕不已,他只知道谢娃娃在跟他竞争,没想到他还有一个隐藏的情敌,“你也喜欢苏豆壳的妹妹?”“苏豆壳的妹妹是谁?”童大嘴说。“苏豆壳的妹妹就是苏豆壳的妹妹,”程眼镜说,脸上呈现贪婪的神色。“一个极为出色的姑娘,要脸庞有脸庞,要肤色有肤色,要眼睛有眼睛,要鼻子有鼻子。”
毛领子帮他把话说完:“要耳朵有耳朵,要眉毛有眉毛,要手有手,要脚有脚。”“对,”程眼镜说,一脸美好的表情,“你说了我正想说的,她是天生的大美人。”“我们去吧?”钩鼻子说,“让这两个猪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你去不去?”毛领子问谢娃娃,“我问你呢?”谢娃娃昂起女孩子样的脸蛋说:“程眼镜去我就去。”程眼镜不为所动道:“我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那我也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谢娃娃站到程眼镜一边说。“你也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毛领子愕然道,“你没搞错啵?”谢娃娃骄傲地回答道:“不,我没搞错。我确实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毛领子大惑不解:“苏豆壳的妹妹真有那么漂亮?”“很漂亮,”谢娃娃说,“她是天生的大美人。”“很漂亮,”程眼镜说,“她是天生的大美人。”“很漂亮,”童大嘴嘻嘻一笑,“她是天生的大美人。”毛领子恼怒他:“童大嘴,你跟着起什么哄?”童大嘴吐吐舌头:“反正我不去那条街。”钩鼻子说:“毛领子,让他们三个傻瓜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我们两人去。”瘦高瘦高的苏豆壳走了进来,一张典型的瓜子脸,一个漂亮的鼻子,一双黑亮亮的漂亮的眼睛盯着他们。“你们都瞪着我看干什么?”他问他们。“苏豆壳,他们都说你妹妹很漂亮。”毛领子问,“这是真的吗?”“哪个说的?”苏豆壳用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盯着毛领子。“谢娃娃说的。”
“我没说。”谢娃娃回答。“程眼镜也说了。”钩鼻子说。“我崽说了。”程眼镜回答。
钩鼻子说:“你刚才说苏豆壳的妹妹是天生的大美人,你说没有?”程眼镜说:“我没说,我崽说过这话!”“哪个敢打我妹妹的馊主意,我就揍他。”苏豆壳正严厉声道。“看你的长相,也可以想象你妹妹的样子。”童大嘴说。“你什么意思?”苏豆壳说,把纯净的目光投到童大嘴的脸上。童大嘴咧开嘴大笑:“他们都说你妹妹是天生的大美人。”“谁也不能打我妹妹的主意。你不能,你也不能。”苏豆壳用他那双漂亮的眼睛盯一眼谢娃娃和程眼镜,又瞪着毛领子:“还有你,也不能。”毛领子笑了声:“我又不认识你妹妹。”苏豆壳盯着程眼镜、谢娃娃和童大嘴:“你们都别打我妹妹的主意。”钩鼻子说:“走吧,我们到那里玩一玩。”
“到哪里玩?”苏豆壳问。“去姑娘最多的地方,”钩鼻子说,“那里的姑娘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你去不去?”
“去。”苏豆壳回答。“你呢?童大嘴?”钩鼻子企图把童大嘴拉去。“我?不去、不去。”童大嘴摆手说。
“你呢谢娃娃?”毛领子说,又加了句,“你反正又得不到苏豆壳的妹妹。”“我不去,”谢娃娃嘿嘿嘿一笑,“我还是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我也要为苏豆壳的妹妹守贞洁,”程眼镜咽了下口水,讨好的模样瞥眼苏豆壳,“要是苏豆壳回到长沙,对他妹妹说我在衡阳的妓院玩了姑娘,那还有我的事吗?”
“你们都不够格。”苏豆壳指出说。“这不是够不够格的问题,”程眼镜说,“这是我个人的态度问题。”“对,我也觉得这是个人态度问题。”谢娃娃附和程眼镜说。苏豆壳本想教训谢娃娃和程眼镜几句,要他们正确地认清自己,不要妄想打他妹妹的主意,但来不及了,因为毛领子和钩鼻子已对他们彻底失望地大步走了出去。
黄抗日也去过那条街,但他没机会干那种事。他在到处客满的情况下绝望地走了回来。那么多大兵,那些大兵在门口嚷着,叫着,为争抢一个姑娘而打起了群架。黄抗日见场合不对,因为那些大兵见人就打,他只是站在那儿就平白无故地挨了六拳。他们甚至都不问他是哪边的,哪个师哪个团哪个营的,拳头就打来了,有一拳还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只好捂着流血的鼻子打道回府。
黄抗日还去过一次,那是一天下午,那已是侵略军兵临城下的日子。他是被毛领子和钩鼻子带去的,两个小兵很想去,又怕班长责罚他们干更多的活,就动脑子唆使班长一并去。他们一前一后地围着班长转,不失时机地对班长绘声绘色地描绘其中一个姑娘,说那姑娘面若桃花,妖媚无比,是天生的尤物。班长不懂尤物一词的意思,问毛领子:“尤物?”
钩鼻子抢着回答:“尤物就是指特别漂亮的姑娘。”班长问:“特别漂亮是多漂亮?”毛领子想了下,形容道:“就是你一看见她,下面就硬了。”班长听毛领子这样说,就萌生了体验一下的淫念,但想起自己在妓院里挨了打,又犹豫不决,“我的鼻子现在还痛,”班长心有余悸道,“我只是站在那里看热闹,都挨了打。”
毛领子道:“我们会保护你,打架我最在行了。”黄抗日也是男人,也想女人,见毛领子这么说,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了。“走。”
毛领子走在他一旁说:“班长,我现在总算睡过女人了。童大嘴、程眼镜和谢娃娃,万一战死了,还不晓得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说这不可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