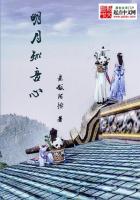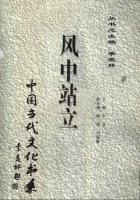庆元三年春,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当年曾权倾朝野的首辅汪中庭去世,死后被满门抄斩流放,成为本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起案件;第二件是,为汪中庭求情的大将军吴峻锋被举发在家中收藏龙袍,下狱三日之后,亦被抄斩。吴大将军孤家寡人,虽未造成如汪家一般被满门抄斩流放的血事,不久之后,闻知此消息的百姓自发走上大街,为他送行。
吴峻锋虽不如汪中庭一般曾权倾朝野,但他战功赫赫,镇守东南十余年,几番击退来袭的倭寇,守东南一方国土平安。不久后,东南百姓在当地为他修建起一座生祠,以示祭奠。
吴峻锋被抄斩时,白璧也去了。她之前从未见过行刑的场景,也从未想过会亲眼看见一个人在面前被大刀一刀斩下头颅的模样。吴大将军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行伍多年,粗布麻衣也掩盖不住他彪悍的体魄和威悍的气势,整个人如一把微锈的长枪,直直地矗立在此地,不弯不折,不屈不挠。这是她从前从未见过的,她见过的男人们,有儒雅端正的,有凶悍威猛的,有精明利落的,却从未有如他这般,锋利却厚重,沉稳而有力的。他就像心里就有自己的标尺,磊落于天地之间,挺拔于众生之中。
他即使是跪在行刑官面前,都要比那猥亵的行刑官要高大。
白璧紧紧握住刀鞘,骨节狰狞出青白的寒色。她此前固然不认识吴大将军,但就是这样看他一眼,她都不会相信此人会在家中藏龙袍。更何况时间竟来得如此之巧,就在他前一天刚刚跪在殿前为汪中庭求情之后。
她几乎欲转身离去,而不忍看到最后亦可。
突然,就在此时,人群中一阵猛烈的骚动。随即,一大批百姓猛地涌上前来,七手八脚地推开围在刑场周围的兵士,向吴大将军涌去。白璧微微避开,稍稍藏到墙角,微微挑了挑眉。
她眉毛向来长而锋利,挑眉时不仅显得凉薄,且还有一分说不清道不明的风流,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她冷冷看着刑场上兵士在推搡间无可奈何撞倒的百姓,看着场面混乱得一时近乎失控——吴峻锋猛地站起来。他双手被缚在身后,站起来时甚至还有一分踉跄,怒吼了一声。
现场人声喧哗,他的怒吼被盖在喧嚣的吵闹声里,吴峻锋脸色通红,四下里望了望,却似乎没有看到想要找的人,又失望地低吼了一声。白璧的耳力要远比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要好,清楚地听见了他两次无奈的吼声——而后,他自己猛地向行刑官的刀锋撞了上去。
他用尽全力撞上去的威力与行刑官刀刃砍下时的威力也相差不远了。破碎的皮肉被卷进风声里,又迅速消散在这人群之中。他黝黑的皮肤染上了滚滚而出的鲜血,被浸染得通红。周围人群仿佛在风声中听见了他的消息,声音低沉了下来,又迅速沸腾,尖叫声和痛苦声交织在一起,让白璧在瞬间都忍不住落泪。
她嘴角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刚刚的嘲笑。
谁都没有想到,吴峻锋在被逼之下,竟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堵死了他自己的生路,也堵死了幕后人的算计。
白璧缓缓凝住一口气,颓然靠在了墙上。远远看着吴峻锋高大的身体重重砸进地上,像一座大山倾倒,令人心惊胆战。白璧不知道人群之中是否有宫中人或两座王府中的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知道这样的情形,甚至亲眼见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所动容——天色欲晚,而大厦将倾。
如水沉烟一般汲汲营营不断算计的小人,在见到这样堂堂正正的牺牲时,会不会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卑微?阴谋不能现于人前,而阳谋却能堂堂正正地一决胜负。吴峻锋在无路可退时与其说是背水一战,不如说是鱼死网破。
他镇守东南十几年,最终换来的不过是一场不甚光明的厮杀。以百姓为开路的前锋,这位一生戎马的将军做不到。
百姓愤怒的呜咽声响起,白璧定了定神,抬步离开。
不出一刻钟,这里发生的事应该就会传进宫中。白璧心想,下一位接替吴大将军的将会是谁?
本朝善水战的将领本就不多,吴峻锋虽然是汪中庭一手提上来的,但他宜陆宜水,早些年在南疆打出了名声,调到了东南之后与倭寇打水战也不怯场,这样的人才,朝中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
且看听闻风声的倭寇会不会趁乱上岸摸一把鱼了。
白璧以心度心,觉得人家实在没道理放着便宜不占,虽说被吴峻锋打怕了,近两年已经不大上岸了,但现在东南可没有主事的将领不是?
短短一个月,这片已经浸透了鲜血的刑场上空,都漂浮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狰狞的气息,令人作呕。白璧走出一条街外,还觉得能隐隐约约嗅到一股血腥气,听到断断续续的哭声和呜咽声。
转过一条街外,就是京城中最有名的“仁义堂”药房。坐馆的老大夫不在,是个中年大夫坐在桌后,低着头在写脉案。此处因为地势较偏僻,人不算多,不如“仁义堂”开在闹区的那家店热闹。但这里的这家店才真正算得上“仁义”,不少看不起病的百姓平日里往往就会寻到此处,开一剂便宜些的药,也能混些日子。白璧只见过城中的另一家,此时见到这一家“仁义堂”,不禁很是好奇。
她在药王谷呆的日子久了,多多少少也学到了些皮毛。她人聪明,记性也好,见过的草药大多也不会忘。虽然不会看脉开方子,但帮人抓药却是没问题的。此时外面也乱得很,这里反倒成了一片安静处。
这一仔细看,却越觉得这看脉的大夫眼熟得很。骨架瘦削,颧骨略高,眼窝较深,不似中原人,反倒是很像……南疆人?
白璧差点脱口而出:“傅……你怎么在这里?”
没错,正是本以为已经被两大王府收入彀中的傅肖。傅肖微微抬了抬眼睛看了她一眼,轻描淡写道:“我四处行医,如今到了京城有什么好奇怪的?”
此处自然不是说话的好地方。傅肖性谨慎,傅川不靠谱,谷中大大小小的事,反倒是时常落在他身上,做事一向妥帖得很。见他如此,白璧当下便明白,此处并非是药王谷在京的药铺。傅肖对此处不熟悉,自然要事事小心。
他这易容术极佳,原本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装扮成中年人,看着也很自然。若非傅肖身上有苗疆血统,有些地方实在遮掩不住,本来应该还可以更好一些。
白璧笑了笑,转身离开。
傍晚时,傅肖果然来访。白璧见惯了他总穿着一袭绣满繁复花纹的长袍,和傅川的极相似,披散着长发,此时见着他穿着简单的黑衣,头发也如中原男子一般挽起一个简单的髻,不由地多看了两眼。
傅肖坐下后,抬眼看了看她,道:“白姑娘看起来还是如往常一般。”
白璧年纪较他稍长,他这人向来严肃,往日里就是不苟言笑的模样,板着张脸叫“白姑娘”寒暄的时候,总让白璧有一种他会和她说什么重要的事的感觉。但实际上,傅肖不过是表情一直如此罢了。这么多年,认识了这么久,白璧几乎还从来没见过他认认真真地笑过一次呢。
但他是傅川最重要的师弟,是他的左膀右臂,也是实际上负责处理药王谷大大小小事的“副”谷主。白璧虽然和傅辞关系最好,却也是因为傅辞爱玩爱闹的性子,但真遇到了事,傅川向来是指望不上的,她还是更信任傅肖,多半都指望着他能出来拿个主意。
就像此时,关系着药王谷的立场,也是四大世家最后的底线,若非当时傅肖身在京城,白璧也不会催着纪行之回去看情况。傅辞年纪还小,性子也还跳脱,不仅不如傅肖稳重,也不如傅肖冷静清醒。傅肖看着冷,实际上也是个内方的性子,药王谷固然习惯与世无争,但也绝不会主动投入到水沉烟这一边。
她怕傅辞会犹豫,却不担心傅肖会犹豫。
白璧问道:“你知道了越家庄的事么?”
时间过了这么久,越家庄的事早就传了出来,只要他有心,就一定早打听了差不多。果然,傅肖点了点头。
白璧给他倒了杯茶,轻声道:“怎么不回去?”
傅肖板着张脸,平平板板地回答:“汪首辅去世的那一天,我不在院子里。有人去找我时,我就藏到了汪大人的棺材里。”
听他这语气,好像这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似的。也亏得当时宫里的人没仔细检查,硬叫他逃过一劫。傅肖看着她,说:“我本来打算风头过了就出去的,结果风头就一直没落下来。”
药王谷现在就像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凋零得差不多了的中原武林,几乎就是一盘散沙,有名望的几位老人不肯做这只出头鸟,傅川年纪虽轻,但药王谷资历颇老。不少人就指望着药王谷能率先站起来呢。
傅肖袖着手看她:“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京城了?”
“看看你有没有被水沉烟掳走。”白璧托着下巴看着他,笑道:“这个时候万一你不小心落在了水沉烟的手里,可就真是个大麻烦了。”
傅肖皱眉问道:“水沉烟是谁?”
他这样一问,白璧才突然发现,水沉烟这个人似乎一直只是存在于他们几个对此心知肚明的人的眼里心中,无法对人言。傅肖一问,她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对他开始解释。
末了,还是言简意赅简单道:“就是背后的大坏蛋。”
傅肖挑了挑眉,猜到这大概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解释清楚的问题,随意点了点头,淡淡道:“此事以后再说。”
白璧“嗯”了一声,又道:“我们两个人,倒可以试试能不能一起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