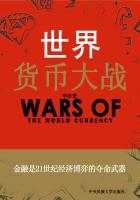郝欢不停地在一颗树下徘徊,手里那铁链“叮咛、叮咛”地一次又一次因它的抖动发出细微的响声,她的手臂也渐渐地有了一种触电之感。
“这个陈章生,面子够大的!今天姑奶奶心情不错,看他要莫慎到啥时候!”索性身子骨向里张望。
“哎呀!郝大管家!有劳你久等了!”
得到了接待令的梁兴急冲冲地跑了回来,脚鞋撞击路面发出“踏,踏,踏”简短而又清脆的声音,象摇摆的挂钟很有规律地振动着。
“啍!算你们还识礼节,懂道理!”
热屁股贴上了冷脸,梁兴脸上似有无数蚂蚁在爬,他扫视了几眼,眼晴飞快地转动。
郝欢阳起头,一脸的不屑。
“哎呀呀!司令家的贵人,八抬骄也难得请来,凡是总有个事先告知,我们局长也好提前做个准备!这也是常理,请勿见怪!”
“哈哈,想不到这小小的警察局,繁文褥节够多的嘛!”她把右手的铁链子交给了梁兴。
“梁副官,陈老二在忙啥?”说话口气之大,让梁兴心头一颤!
“你说我们的陈局长啊!他啊正愁没有人唠叨唠叨,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他接过那拴狗的链子“我们局长交待过了,要好生对待这条狗!”说完他“嘿嘿”地笑了几声。
“它叫什么来着?”梁兴拍了拍脑门,“哦!对了,你看我这记性!”
“黑虎……”
“黑虎、黑虎……”
嘴里的喊声象音符:“D0rai,mirai……”很有节凑感!
郝欢看了看那似笑非笑的梁兴,嘴里的门牙一开一闭,一副苦瓜脸,象霜打了的茄子,不带有私毫的感情,骨子里透射出来的尽是冷漠。
“我们局长在办公室恭候你的光临,向前走,转过弯就到了!”
说完,梁兴向另一条路走去,不一会儿响起了狗叫声。
“汪……”
“汪汪……”
郝欢扭动身子,屁股很自然地愰动起来:“哼,小梁子,小心饲候那狗!不然让你走不得干净路!”
她细手向着那远去的背影往下拍了一下:“姑奶奶这就去会会这个爱花的陈老二。”
“嗡嗡……”
“啪”的一声响,在耳边来回飞舞的蚊子被她细手送上了西天。
“你这小东西,姑奶奶岂是好吃的,哼!”
陈章生半迷着眼,大阳光线通过屋顶缝隙照射下来,形成一条条圆柱形的小光柱,在青石板洒下一个个小光斑。
一条黑色的影子慢慢地从石板的一角布满整个板块,象落帐的围幕徐徐关闭。
“咝、咝!”一双粉红色的绣花鞋在那旗袍下交替移动。
一条沙巾半掩着脸,胸前两只刺绣的蝴蝶在那挺拔的山峰处跳动,细腰随着两跨的摇摆一伸一缩,流动的空气被一点点的挤压,几只蜜蜂似的小虫子扑闪着翅膀,传递着这奇异的芳香。
“陈局长,陈哥哥,小妹一路巅波好不容易走来,你也不来迎接,迎接!”她把细纱巾向陈章生飞了飞,嘟着嘴唇,流盼的双眸传送着一阵阵噬骨销魂的秋波。
“哎哟!”郝欢正沿着台阶往上走,裹在旗袍的粉腿一歪,她连忙用右手趁着,身体达拉成一张弓,娇慎地停留在那个地方,粉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跟。
陈章生站了起来,舔着那向外隆起的大肚子,望了望看似修女的郝欢,眼角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哦约!这不是薛司令家张太太的侍女郝欢吗?”
“梁兴,小梁子!这真是跑哪去了?”他向远处伸了伸勃子,似乎在寻找救援的人。
阳光下,那黑色旗袍里露出粉脚斜靠在阶梯边,郝欢的脸上是乎是出现了痛苦的表情。
陈章生迟疑了几分钟,很显然她是被歪了脚了。
不过,过了一会儿,郝欢慢慢地直起了身子,一手还在右腿上捏了捏,走进了办么室。
“快请坐,这该死的台阶,让你受苦了!”他脸上木纳,看不出任何表情。
“局长,你找我?”跑得上气不及下气的梁兴摸了一把额上的汗,望着陈章生。
“快给这位郝女士柔柔腿!”陈章生用手指了指。
“不必了,谢过了!我来主要是向你通报两件事!有水喝就足以!”
“哦!小梁快给她沏杯茶!”他用手掌对着自己的脸摇了摇:“这鬼天气,热就不说了,干燥得让人作呕!对了,你是不是又来向我讨要那盆花吧?”
“你这个陈二哥,那都是哪百年的黄历了!今天有重要事情相告,你升官,发财的好日子来了!”她一面说一面向他抛了个媚眼。
陈章生拦住了梁兴的手,从中抢过茶杯,近乎殷勤地递了过去。
“不急,慢慢讲!”
郝欢伸出纤纤细手,手指向上,伸了过去接过那冒着热气的茶,然后很小心地放在身边的桌子上,挑了一个很洁静的凳子坐了下来。
“不会是你发现了革命党吧!”陈章生坐回自己的位置,面容严肃:“小梁,这儿没你的事,你出去吧!”
“好的!陈局长,有事呼我!我去给你那花浇浇水,让它也快活快活!”
陈章生点了点头,“你这鬼机灵,去吧!有事我叫你!”他对他向外挥了挥手。
……
小小的三轮车上韩通和麻杆被卡在座位里,三面被围着,刚才被烟薰过的地方余热依然保持着!
韩通望了一眼抚他上车的少女,清了清喉咙:“姑娘,你还挺大胆的!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总是姑娘长姑娘短的叫,多不方便啊?”韩通微笑道。
“我叫……”姑娘张英飞刚要回答。
“啪,啪,啪……呜,呜!”小巷西头的人影闪动,好象有大批的人员在街面聚积。
车身后那不远处冒烟的地方突然发出“呯”的一声巨响,拉车的蒙面大汉转过身,通过他们两人的缝隙向远处望去,脸上的表情似乎有惊异。
麻杆的三角眼闪了闪,看见了那瞬间转变的复杂的表情,还有不时传来密聚的奔跑声,猜想自己的同伙快要来到,身子也不那么抖了。
“我说,你们投降吧,如果投降,我去向上司求求情,免你们死罪,怎么样?”
随后那突然的爆炸声,吓得他勃子一缩,本来细细的身子这时象筛糠时那样跳动:“你们……”
“格老子的!让他们追吧!不玩了!”汪兴迅速转过身去,双臂只轻轻一用力,那两个轮子就“咕咕”地旋转起来。
少女张英飞,麻杆和韩通加上蒙面大汉汪兴转过小胡同,眼前是一条大街。往日是人潮涌动,歌声笑语。今天却大不相同,气氛显得很紧张。
远外,一条封锁线已经形成,五六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十来个警察正在盘察行人,没有合法的证件休想通过。
转过头来看另一边,几个骑着自行车。腰挂二十响的盒子炮的家伙正气势汹汹而来,他们是便衣队,是更让人恐惧的家伙。
对面,是另一条更小的胡同,全长二百多米,可惜的是一条死胡同。前面不远处就是汪兴的杂货铺店,卖一些烟、酒、茶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咣档,咣档。”是上门板的声音,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门相继关闭。
没有时间考虑了,摘掉蒙面巾的汪兴急促的说道:“快,下车,到我的店里暂避一时,等过了这一阵在说。”
四人鱼贯而入,不甘心被擒的麻杆被汪兴一脚踢了进去。
“咣档,吱呀!”店门关闭。
“快,进里屋,把门插上!”汪兴领着大家穿过前堂进入内室。
四人急急进入里屋,光线较暗。等大家适应过来,只见里屋的家俱很少,墙角处摆着一架老式板床,床上两条破棉被堆在了一起,高高的麻布纹帐,罩门敞开着。奇怪的是:面前的墙上挂着一幅观音像画,这也太大了吧,像一扇门。
“扑通……”韩通在也支持不住,连带麻杆倒在了地上。
“快把他扶起来,我去找点纱布,好止血。把手拷打开,拷住那个瘦子。”汪兴说罢,又转身出去了。
“把手铐阴匙交出来!”姑娘张英飞历声喝道。
“小姑奶奶,我那有什么阴匙,都在刚才那个胖子身上,你这个同伙……”
“啥?”姑娘双眉倒立,杏眼圆睁。
“我,我说错了。你这位同伴太心急,把我们两个的手铐在了一起,我是贱命一条,随便怎样都无所谓,却连累了这位好汉爷,好汉爷。你说是不是?”麻杆可怜巴巴的说道。
“呸!你说得好听,一肚子坏水。”张英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那伪善的嘴脸。
“咳,咳,咳。”韩通咳得喘不过气来,好一阵子,姑娘又是拍背,又是抚胸。
鲜血又从衣服里渗了出来,韩通感觉得到,那颗子弹被肌肉卡住了,既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伤到大动脉,不幸中的万幸,只是头有一点晕,也许是失血过多。
“吱呀”一声响,门猛的被推开。汪兴走了进来,脸色很不好看,他左手拎着一壶二锅头,右手拿着一卷纱布,来到韩通面前:“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止血,我们时间不多了,那些家伙正逐门逐户搜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