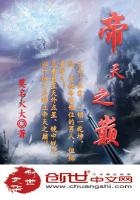“各位旅客,各位旅客,洛阳站到了,由于列车停靠时间较短,请各位旅客不要在站台处逗留,需要下车的旅客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提着行李,往川走在最前面,南风和韩盛繁拉着拉杆箱紧跟着往川。在洛阳站下车的旅客不算少,大多数都是背着大包小包的打工者,像韩盛繁他们这样出来玩的还真不多,毕竟假期已经过了,往返的都是打工者或者学生。
出了站没走多远,往川就已经和门口的一个面包车的司机扯起皮讨价还价起来了,韩盛繁和南风站得远远的,看着往川和面包车司机吐沫星子横飞。
“南风……你听得懂河南话吗?”韩盛繁弱弱地问了一句。
“差不多……毕竟之前也听往川讲过……只是……”南风的眉梢也抽了抽,“没想到……连发起来这么可怕……”
“……”
很快,价格谈妥了,往川招呼二人上车。这是一个七座的面包车,加上司机,一共四人,空间还算宽敞,只是车内的气味不是太好闻。南风伸手想拉开车窗,却发现车窗被完全封死,根本拉不动。南风看着贴着黑色玻璃膜的车窗,皱了皱眉。黑膜比正常的镀膜玻璃的膜都要厚一些,从外面完全看不到车里的情况。
封死的玻璃,厚厚的黑膜,这面包车是怎么回事……很快,南风就得到了答案……面包车的大嗓门的河南司机扯着嗓子开着车走走停停,没开出站门,就又一连串的拉了五个顺路的人,接着,九个人“挤挤攘攘”地出发了。
这这这,严重超载啊,好挤……南风坐在窗户边,几乎是贴在车门上的,韩盛繁被夹在人中间,左边是南风,右边是抱着一个四五岁孩童的女士,怀中的小孩一路都在哭闹,在不大的车厢空间里拼命挣扎,使得这一程简直难受。不光如此,车厢内还有两个胡渣男一路都在吞云吐雾,把整个密闭空间浑浊不堪的空间搅得无比刺鼻。更糟糕的是,面前明明是平原笔直的公路,可这面包车司机还把车开得“跌宕起伏”,终于,半个多小时后,车停了,车门一开,南风和韩盛繁几乎是之间蹿出去的。
“恁俩还好吧。”往川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看着半天都没缓过来劲的二人,嘿嘿的笑着。
“到……到了么?这是哪……”南风缓过来的比较快一些,脸上渐渐浮现了一点点血色。
“车(chāi)进不去,咱再走一截就差不多到了。”往川摇了摇手指,露出一口牙。
走路总比坐那种车好……韩盛繁和南风默默拉着行李,走在乡间的土坷垃路上。往川走在最前面,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
“俺北方的天比恁那边干的多,一会进屋了多喝点茶。”
“……”的确挺渴的。韩盛繁舔舔嘴唇,环顾周围的环境。因为是初春,看不到荠麦青青的场面,不过许多新翻的田埂整整齐齐的,远远望去褐色的图案还是颇为蛮壮观的,道路两旁的树还未发芽,光秃秃的树上密密麻麻的林立着胖墩墩的麻雀,远远望去,给人以“丰收”的错觉。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与鸡鸣,或者小孩的啼哭与猫儿的嚎叫,这是乡间独有的风景与声音,也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本色。
村落之所以称为村落,是一个地方各家各户都聚集在一起才形成的部落一般的组织体。往川虽然姓“往”,很罕见的一个姓,在这里却常见的遍地都是。这个村儿的人都姓往,甚至一家的男女老少,都是“往”姓人。
往川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他是大伯供他上的大学。乡里民风淳朴,家家户户大白天都不锁院门,推开门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一条浑身漆黑,站起来几乎比人还高的立耳大狼狗,以至于南风的枪都快掏出来了,而韩盛繁更是退了几米远。
“大毛,不认俺啦?”往川拍着狗头,握了握那那狗的前爪,就像在和人握手一样。
“噢嗷嗷,汪呜哦呜……”大狗嚎叫着,嗅了嗅往川的味道,接着,琥珀色的狗眼里精光一闪,铁棍般的尾巴剧烈地摇了起来。
“川子,是小川子吗?”屋内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接着一个弯着腰的佝偻老人便推门走了出来。
“大伯,俺不是给你打电话说俺今儿带同事来吗?忘了?”往川连忙迎上去,扶着老人走下堂屋的台阶。
这是往川的大伯?看起来更像往川的父亲一般,眉眼都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更巧的是,两人左额角处还都有一块浅色的疤痕。往川那时是被子弹擦了一下,而这位大伯为什么也会有一块疤就不知道了。
尽管屋外是接近零下的温度,屋内却是暖烘烘的。往川的堂哥出去打工昨天已经走了,而堂妹也开学了,现在家里也就往大伯一人和大毛一狗了。
大伯的话不多,倒是往川的话不少,整整一下午,都是往川在给大伯讲重庆的事情,不过对于SWP的工作部分,被各种各样的内容替换掉了,要不是南风和韩盛繁压根一起经历过的,完全听不出丝毫猫腻。
晚饭的时候,往川的堂妹也回来了,小丫头是个在上高四的学生,匆匆吃了饭,寒暄了几句就头也不回地往学校奔了。
“小川子你可是俺家最有出息的娃咧,可给杏儿做好榜样啊。”王大伯笑呵呵道。
“俺带俺同事在庄里转转。”往川似乎才意识过来他是带着两个人回的乡,而不是自己回家省亲。王大伯也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从怀里拿出烟,递给韩盛繁和南风,很歉意自己冷落了两位客人。
“没事,难得往川回家看望您,多聊聊应该的。”韩盛繁慌忙摆手,和南风往川一起走出门。大毛趴在地上,抬头嗅了嗅三人的鞋,又趴了下去,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天黑了白(别)走太远了,夜里咯斗白(都别)去二塘。”临出门了,往大伯还不忘探头嘱咐一句。
“知道咧,又不是小孩儿。”往川撇撇嘴,可脸上笑意不减。
“二塘?”韩盛繁小声问道。
“就是村后头儿的沟,村里挺邪的地方。不过咱干这一行也不怕这个。”往川耸耸肩。
“那……去看看吗?”韩盛繁半开玩笑地问道。不过,刚一说完,就看见往川忽然敛起笑容,一副严肃的表情:“最好别那劲,咱几个不怕,不过可能会给别人添麻烦的。”
看着韩盛繁和南风都一副“求解释”的表情,往川抽出根烟,点上火,猛吸一口,缓缓吐出:“俺往家村得有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塘也管追溯到清朝,不过在那时,好多村山高皇帝远的,啥事都村长说的算,村里有村里的私刑,俺村也不例外,这个沟就是专门用来处置犯了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村规的人,因此这个塘又叫‘死人塘’。”
“私刑?淹死吗?”韩盛繁一愣,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听到这样的故事,“那,那个塘岂不是会闹鬼……”
“闹鬼,闹的还凶咧。一到夜头七点半往后,村里就几乎没人在路上走了,约么九点后后谁敲门都不给开。”往川笑了笑,指着旁边的一座宅院的大木门,“恁过来看这玩意。”
韩盛繁和南风凑了过来,大木门上蓝色的漆已经发白,剥落了一大片,几乎看不出原样。门上贴着的门画却是崭新的,在门框上可以看到一排泥巴人,有大有小,看不清五官。韩盛繁准备伸手拿下来一个,却被往川拦住。
“土人偶?”南风个子是三人中最高的,加上视力超级好,看的清楚一些。
“嗯,土人偶,里面包的是乳牙。”往川摸了摸下巴,“这玩意用艾草水浸泡,涂了油,俺们本地称它‘泥奴’,如果有恶鬼上门用这玩意替死的。用咱现在的眼光看,这玩意属于傀儡,是以人的乳牙为傀儡核心。乳牙你们知道吗?”
“嗯……就是小时候掉的牙。怎么了?”韩盛繁踮脚看着那一排泥奴。
“指甲盖不行吗?”南风问道。
“不中。”往川笑了笑,“因为指甲只是人的生长代谢物,是死物,而乳牙,是活的。”
“哈?”头一回听说,这掉下来的乳牙还是……活的?!
“咋说咧?牙算得上是人的骨头,人骨可是有魂的。乳牙算得上是体魂的脱落物,含有魂魄碎片的,用于做替身傀儡的成效远大于头发或者指甲。具体俺也说不清,反正用的乳牙。”往川挠了挠头,指着泥奴,“反正这玩意摆门口,屋里人就可以高枕无忧,除非里面人造孽太深,不过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那种事。到后来全中国解放,俺村接受思想教育,村规就废了,这塘也废弃了,还请过人做法啥的,后来没传过啥闹鬼的事了,好像太平了,毕竟鬼啥的也难以在现世逗留太久,这也不是阴地,聚不了啥阴气,不过这塘还是一般少有人靠近。”
“那……为什么不把塘给填上?”韩盛繁问道。
“唯一的怪事就怪在这儿。”往川耸耸肩,一脸无奈的样子,“这塘填不了。”
“嗯?无底洞吗?”南风小声问道。
往川一摊手:“到没恁邪,不过,填上之后老冒烟,还把附近的荒草地给点了,一直烧到田里,只能挖成塘子,荒废在那。”
“去看看。”南风居然提出这样的想法,以至于往川和韩盛繁都愣了一下。这家伙从来都没有好奇心和“冒险”意识,这是怎么了?
“不中些,等明个天亮了带恁俩去。”往川摆摆手,一脸不情愿的样子。
看着往川一脸忌讳的样子,南风点了点头。韩盛繁想再问一些什么的,不过看了眼往川的脸色,也就没有问了。接着三人便继续游览往家村。
往家村不大,大片的土地都是田地和鱼塘,村里的人家贫富差距还是有的,三人在村东头见到只有两间瓦房的破烂老五家,也有三层小洋楼的什么养殖厂厂长家。村里的设施不多,连学校都只有一所小学和中学的,连幼儿园和高中都没有,往川的堂妹是在邻村郑湖村的高中上学。往川说他那时拿到警察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后,简直成了村里的风云人物。南风还稍微能理解,而在县城里长大的韩盛繁觉得很不可思议。三人边走边聊地在大约八点的时候走回了大伯家,天已经全黑了,路上连个路灯都没有,只有一户一户的人家点着橘色的灯泡,仿佛在黑暗中摇曳的烛光般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