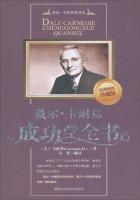亲自出来相迎,似乎是为了告诉别人他韦承庆不是嫉贤妒能之辈,非常欣赏比自己有才华的人,洗脱自己的嫌疑;随后韦承庆大赞寿桃为祥瑞,将他高高的捧起,似乎就是为了下一步将他狠狠地摔下;而后穷追不舍地询问寿桃出处,似乎在找破绽,其目的现在想来大概是为了让余问心听见,从而想出对策诬陷于他。
于是余问心站出来了,看似是给韦使君添堵,实际上是玷污他的清白,让他的德行在众人的心中留上污点,或许余问心采用的方式有些无理取闹,但只要他不能拿出证据,那在众人的心中就会疙瘩存在。
如此一来,只要余问心提出每人赋诗一首为韦使君贺寿,继而把韦承庆搬出来,那韦承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站出来开这个头,或许有人心里会不服,但他德行有失,韦承庆的阻力会小很多。
但让韦承庆意外的是,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破解办法,并且如此有魄力,当着韦使君的面把送给他的寿礼切开,破了他布的局。不过想来虽然有这个意外出现,但他的阴谋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只是结果说不上顺理成章而已。
只是片刻功夫,王勃就思考出了这么多问题,若是这事被韦承庆知道,指定吓傻。
而他的猜测也的确与事实相差不远,别看韦承庆表面上没什么,实际上他和余问心一样非常嫉妒王勃,甚至比后者还要嫉妒。
他把王勃今日得来的名气都归咎于他父亲的偏心,认为王勃能有今日,是因为他父亲的帮助。如果他父亲早年这样帮助他,那他岂不也早就名扬天下了,何苦到现在还默默无闻?所以他想不通,他是他的亲生儿子,他不帮他亲生儿子,却去帮一个外人,凭什么?
他今日的这番举动,既是针对王勃,又何尝不是对他父亲的报复?他就是要让他看看,看看他一手提拔的天才,是怎么被他踩在脚底下的。
而余问心恰巧也跟他一样目的,于是两人就结成了一伙,方才有今日这个结果的出现。
虽然结果不大理想,但他至少站出来了,就在王勃的身旁,而王勃只能当他的配角,他才是主角。只要接下来他再在赋诗上压王勃一筹,那他赢的就不仅仅是王勃这个人,还有他的名气,他的名气将会被他赢走。
事实上,他早就算好了这一天,他算到王勃会来绛州参加院试,最近几天就会抵达,所以他提前几天就在运作,打算在绛州办一场文会,将王勃引来,然后打败他,扬名立万。至于诗作,他也老早就准备好了。
只是没想到王勃今天就来了,而且两人还是在这样的场合中相见,这可真是老天都在帮他呀。
他就不信了,他早准备好了诗作,而王勃什么准备都没有,王勃凭什么还能赢?
想到这里,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韦使君看了看余问心,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子,眼底闪过一道精光,显然已看出了端倪。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出面阻止。
他看向王勃,不禁一怔,本以为他脸色一定不大好看,还不知如何面对他,却没想到他竟然浑不在意,依然扇着他的扇子,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
接下来在余问心的张罗下,莺莺燕燕穿插其间,不一会儿,每个人面前的案上都摆上了文房四宝,不等韦承庆下笔,众宾客都已经开始酝酿了。
作诗贺寿,对那些文人雅士来说不是问题,但在座的虽说都是整个绛州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也不乏一些毫无才学的土豪之流,嫖妓还行,作诗真是难为他们了。
韦承庆早在好几天前就已打好了腹稿,此刻只需照本宣科便成,但他毕竟不能做得太过醒目,让人怀疑,所以也佯装酝酿了片刻,便提笔蘸墨,在纸上书写开来,动作一顿一行,很有气势,仿佛才思敏捷、文不加点。
他一动笔,满座宾客的目光被都聚集了过来。王勃和他此刻没坐在一块儿,所以也不知他写的什么,但是王勃却从他挥笔的动作中看出了他强大的自信。
他不禁有些奇怪,曹植七步成诗,故而流芳后世,而他似乎比曹植还厉害一些,连七步的时间都没用到便开始提笔书写开来,这样的一个人按理来说不应该在大唐诗坛上默默无闻才是,可在大唐历史上为何从未见过他的名字?
但转念一想,他顿时便明白过来了,韦承庆既然能煞费苦心地让自己获得这个出头的机会,那为何不能提前就准备好诗作呢?可韦承庆凭什么就能保证他作的诗能胜过他?想来大概他也是一个自负的人。
曾经他看唐代史书上关于韦思谦的记载时顺带留意了一下他的大儿子韦承庆的简介,书中对他性格的评价就两个字“谨畏”,所谓的谨畏是说谨小慎微,这便不难理解他在这次针对他的阴谋中扮演的角色为何如此低调了。
至于说他自负,书中倒没明说,但是从他的生平事迹里不难看出这一点。不但如此,他的品行似乎也有问题,不然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就不会与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交往甚密了。
张易之、张昌宗是谁?乃武则天之面首,也就是男宠,恃宠而骄,权倾朝野,**不堪,无恶不作,与这样的人交好的,又会干净到哪里?
之前王勃第一次见他,被他的表象迷惑,一时竟忘了把他与历史上的韦承庆联系起来,故而被他算计。
韦承庆提笔到收笔可谓一蹴而就,须臾之间便已成诗,众宾客借惊奇不已。
“韦郎君文不加点,须臾成诗,堪比曹植七步成诗,果然大才。”
“对对对,不知韦郎君写出了什么好诗,还请展示于我等,好教我等大开眼界啊!”
面对众宾客的恭维声,韦承庆喜不自禁,招了招手,便有两个婢女将诗卷展开,向众人展示。
韦使君捋了捋长须,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自己的儿子被人赞赏,他自然高兴,虽说儿子为了得到这个机会使用的手段有点不光明,但如果他真能在诗才上胜王勃一筹,他倒是可以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为了让楼上的宾客都能知道纸上写的什么,韦承庆不好出面,所以由余问心代劳将诗句念出来道:
当筵美奏霓裳舞,常爱南山坐翠微。
人似孔融宜服政,年如卫玉已知非。
画楼日照才名远,紫庐东向德闻馨。
共羡向平婚嫁毕,登山临水醉忘归。
余问心念毕,满楼宾客尽皆叫好,韦使君也满意地点着头。韦承庆不住地拱手,脸上的笑容比菊花还要灿烂。趁着拱手的间隙,他睨了一眼王勃,却见他根本没看他,而是翩然扇着折扇,望着满楼宾客,嘴角带着淡淡似讽的笑意。
韦承庆嘴角抽搐了一下,暗自冷笑一声,给余问心递了一个眼色,余问心会意,于是又道:“既然是给我舅父韦使君贺寿,那这所作之诗自然是即兴的为好,若是已经用过的,那是对韦使君的不敬,所以某想出一个抓阄的办法,在每片纸上写上押韵的字,放进签筒中,抽中什么样的字,就用这个字的韵作诗,这样岂不妙哉?诸位以为如何?”
众宾客自然只有叫好的份,难道敢说个不字吗?倘若如此,岂非是承认自己没才华,即兴作不出诗?想要用昔日所作之诗或者别人用过的诗滥竽充数?那不是对韦使君不敬吗?
“四郎,不知他又要使什么坏,你要小心了。”月奴提醒道,脸色担忧。
王勃点点头,安慰道:“放心,任凭风浪起,某稳坐钓鱼船,且看他要耍什么花招。”
刚说完话,肩膀就感觉有人碰了一下,王勃回头一看,却见牛大正捂着肚子一脸委屈地望着他,道:“四兄,俺饿了。”
王勃不禁有点心疼了,把他带来本来是想让他吃点好的,不曾想碰见这档子事,反成了活受罪;而且来之前有言在先,禁止他放肆,所以牛大才没“大开杀戒”,一直乖乖地坐着,不过这也跟几案上没几样菜有关。
可现在不是时候,王勃也没有办法让他吃饱,所以只能安慰他道:“牛大,再忍忍,等会儿四兄定让你吃饱。”
牛大嘴巴一瘪,撒气地偏过头去,抱着臂膀不理他了。
王勃苦笑不已。
余问心将签筒准备就绪后,派十几个婢女各自捧着一个签筒走到那些宾客面前,让他们伸手抓阄。
轮到王勃抓阄的时候,却是韦承庆亲自捧的签筒。
看着韦承庆脸上洋溢的热情的笑容,王勃忽然有股一拳打爆他脸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忍住了,把折扇一合,却不忙着抓阄,而是笑眯眯地拱手道:“有劳韦大郎亲自送来,某真是受宠若惊啊。”
“哪里哪里,王四郎说笑了,某把你看作朋友,亲自送来是应该的嘛。”韦承庆笑容可掬地道。
“呵呵,这怎么好意思呢?不过韦大郎的诗作得可真好,某只怕拍马难及啊。”王勃又拱了拱手道,完全没有要抓阄的意思。
因为王勃坐着,所以他要保持着弯腰的姿势才能让王勃够得着签筒,此刻他感到脖子和腰有点僵硬了。
“王四郎过谦了,你才名远播,诗才了得,每诗皆为传世佳作,某才是拍马难及啊,哈哈。”韦承庆笑容有些僵硬地道。
你还知道啊,王勃腹诽道。
“你该抓阄了。”生怕王勃再崩出什么话来,韦承庆赶忙补了一句道。
“哦,瞧某这记性,与兄畅谈,竟忘了这事,且看看某抓出的是什么东西。”王勃装作才醒悟的样子,提着长袖,将手伸进签筒里。
半响,韦承庆笑容僵硬地道:“王四郎,你要抓到什么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