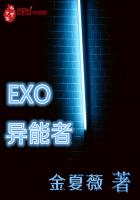该来的总归要来,马沫莲进来的时候,杜寒桥总觉得她会蹦蹦跳跳的跑到自己父亲那欢快的叫一声杜伯伯,然后再拿眼角瞄自己。只是时间永远不会定格在7年前,现在的马沫莲已经快嫁为他人妻,拆去了满头的小辫,盘起了长发,脱去了精悍的皮甲,穿着端庄的淡黄色丝质长裙,她只是矜持的问候了一声:“杜伯伯。”倒是一虎背熊腰,天生一对牛眼,睁大了圆圆的年轻人,快步上来拍着杜寒桥的肩膀,呵呵的傻笑,说:“杜家兄弟多年不见啦,看看我马翼是不是比原来壮了许多。”杜寒桥起身,同样拍了拍马翼的肩膀,说:“当然结实了,你现在可是被称为西北三公子之一啊,年轻一辈中,已是罕有敌手了。”马翼两只牛眼瞬时笑的弯成了月牙,说:“杜家兄弟原来老说我瘦,我这几年下的最大的功夫就是把自己吃壮了,功夫什么的只能排第二。”两人这么有一处没一处的瞎扯,听得后面一人咳嗽了一下。马翼这才一拍脑袋,让过身来。杜寒桥这时面对面的看着马沫莲了,正当不知说什么好时,却又听见一声咳嗽,原来马沫莲身旁还站着一人,此人一身青衣长袍,肤色透白,比之马沫莲还要白上三分。背后一把三尺长剑,似儒雅书生,又似悍勇游侠。一看便是个人物。马翼赶忙给长辈介绍,:“杜伯伯,这为便是人称玉剑的张伦宿,是舍妹的未婚夫。”未婚夫,这三字让杜寒桥的眉毛抖了一下,也只是抖了一下便再毫无表示了。马沫莲低着头站着,不知是有心事,还是含羞。张伦宿朝着杜墨行与马阔野恭敬的见礼作揖,说了句:“见过二位伯伯,小的这厢有礼了。”杜墨行朝马阔野竖了大拇指,说:“西北三公子,你们马家就有两个了。”马阔野哈哈一笑,说:“这都是虚名,什么三公子,这三个孩子里,我看我这女婿和我这傻儿子,都比不上另外那个公子,血枪王篱山,人家可是为我大明苦守西北边关,那帮为非作歹的胡虏一看王家的旗,那便是招魂的幡啊,这几年在边关这王篱山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啊。我这俩孩子,差人家远着呢。”
听得老父如此说,马翼只是边挠头边傻呵呵的笑,张伦宿也在笑,只是杜墨行请他们入座,这张伦宿坐下将背后的剑拿下来的时候,紧紧的攥了一下剑鞘,指节都因用力瞬间的发白,但当剑放到桌子上,手离开剑鞘时,张伦宿似乎整个人都轻松了,笑的更自然了,而且还则过头对着身旁的马沫莲悄声说着什么,马沫莲居然红着脸偷笑了一下。杜寒桥只是蒙头喝茶,而身后的苏岸柳又是长长叹了口气,引的杜寒桥放下茶杯回过头偷偷的拿眼瞪他,苏岸柳立马做了个缝嘴的手势。
整个嘘寒问暖结束了,杜寒桥告辞时,没有再看马沫莲一眼,逃难似的离开了正厅。苏岸柳搂着杜寒桥的肩膀说:“我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走去‘醉半宿’喝一盅。”
当张伦宿与马沫莲结伴离开正厅,出了杜府,往自己的临时居所慢慢行走的时候,张伦宿的脸一直是铁青的。马沫莲似乎心情也同样不佳,两人许久不曾说过一句话。直到张伦宿觉得四下无人,这才停下脚步,马沫莲看自己的准丈夫突然停步,自然而然的也站住看着张伦宿。路两旁是些假山和亭台,偶尔听得小鸟展翅飞过的声音,再无其它声响。张伦宿看看马沫莲,突然笑了,虽说张伦宿天生玉面、剑眉星目,长的可谓仪表堂堂,但这笑的却是极难看,便似那一桌的佳肴,偏偏时间太长变馊了的感觉。张伦宿的笑只是在掩盖他的愤怒。“我这人的直觉很准”张伦宿笑着,但眼睛却死死的盯着马沫莲。
“为何突然说起这个?”马沫莲一愣神,问道。
“我记得你在这西云城陪着你哥哥待了三年有余。”
“嗯,怎么了?”马沫莲看着张伦宿,皱了皱眉头。
“从你离开西云城,我遇见你,我便开始不停的向你马府提亲,一只提了五年,你方才答应。”说完,张伦宿笑出了声,只是笑的有些干涩。
“怕是你等的那个人,五年间都不曾过问过你吧,灰了心,才想起了我。”
马沫莲听完,虽说今日在杜府正厅因为看见杜寒桥,本来觉得早已死绝了的念头,在看见杜寒桥,看见他还戴着自己给他做的眼罩时瞬间的崩塌了,他是真忘了我,还是一直惦念着我,为何五年不曾来过哪怕一封书信,可偏偏何为又戴着那个眼罩。一时间竟然有点手足无措,只得不停的提醒自己,自己已经是有了婚约的人,不为别的,这张陇会也不是他马家寨说能惹就能惹的。所以听得张伦宿如此阴阳怪气的责问,本来性格彪悍的马沫莲硬生生的压住了怒火。
看见自己的未婚妻如此表情,张伦宿觉得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了,“这杜二公子,听说剑法过得去,勉强算的一流,虽说瞎了一只眼睛,长的可也算端正。”
听得张伦宿这样说,马沫莲急忙打断了他的话。“张郎,莫要胡思乱想。我答应了你家的婚约,便没有反悔的念头。如若反悔,当如此石。”说着马沫莲竟然抽出腰间的弯刀,转身横劈,路旁假山边的石头,瞬间被弯刀美妙的弧线扫过,应声变成两块。马沫莲收刀表情坚决的看着张伦宿。
这时张伦宿突然将脸贴的很近,几乎鼻尖对着马沫莲的鼻尖,冷笑着说:“这话说的好,这刀耍的也还行,但怎么都不像在说婚约,好似再说两个帮派歃血为盟的大事哦。”
说完张伦宿自顾自的往前大踏步而去,留下马沫莲一人对着那被斩成两块的石头发呆,这时候应该哭吧,马沫莲如此问自己。可是却没有一滴泪落下来,这刀是自己挥的,这路也是自己走,哭?这般没意思的事情,马沫莲是不屑做的。
夜晚,醉半宿酒楼,二楼的包间里,杜寒桥和苏岸柳喝了很多酒,酒桌上,地上空着很多空酒壶,苏岸柳已经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而杜寒桥却依旧清醒着。
“想醉不能醉,好似中秋云遮月啊。”杜寒桥长叹一声,晃着手里的酒壶,脚搭在桌子上,用剑鞘捅开了窗户,畅快的夜风涌了进来。
此时有人推门走了进来,“杜二公子好雅兴啊。”见来人青衣长袍,发髻高束,面似白玉,大大方方的坐到了空着的位子上。
杜寒桥毕竟也是受过夫子几年戒尺的拍打,与旁人之间的礼仪还是知晓的,急忙将腿从桌上拿下。起身拱手说:“原来是伦宿兄。”而这张伦宿却依旧大大咧咧的坐在位子上,随随便便的拱了一下手说:“杜二公子莫要如此,坐,坐啊。”看见这人如此做派,杜寒桥的脾气也上来了,不仅坐了下来,而且那脚又搭回了桌子上面。杜家二公子的做派始终便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反过来的话,同样如此。
张伦宿看着杜寒桥搭在桌上的脚,笑了笑,说:“早就听说西云城的龙骨剑高深莫测,而西云城的龙骨剑士也是这江湖上人人敬畏的剑客。我张某人心仪已久,只是这世间沽名钓誉之辈多如繁星……呵呵。”
看着张伦宿的冷笑和那意犹未尽的话意,杜寒桥斜靠在椅子上,手里晃着酒壶,右眼的眼神已经渐渐的冰冷了起来,这眼神如果林牧风在场,便会提醒张伦宿莫要再说下去,在榆中的客栈里,在孟顽仙的院子里,杜寒桥将人斩成碎块的时候,那眼神便是这样的冰冷。
张伦宿似也感觉到了杜寒桥的杀气,但他以为,杜家公子还不会爆裂到在酒楼里杀了自己这个赶来祝贺他妹妹新婚的客人。
便接着说:“我还听说过每个龙骨剑士手里的剑,在打造成功的时候,便有上天赐字与剑身。每把龙骨剑的名字都是由天授于。真是奇哉妙哉。”说着张伦宿的身子微微前倾,看着杜寒桥问道:“不知杜二公子的龙骨剑叫什么名字?”
杜寒桥冷冷的看着张伦宿,许久突然一口喝干了手中酒壶里的酒,随手扔到一边,说:“我没有龙骨剑,我不是龙骨剑士。”
听完这句,张伦宿哈哈大笑:“杜二公子在消遣在下吗?堂堂杜家二公子却没有龙骨剑?”
杜寒桥也笑了:“谁说杜家的人就必须得有龙骨剑?”
张伦宿止住了自己的笑,一副嘲弄的表情看着杜寒桥说:“当然杜家的人无须人人都有龙骨剑,就好象我青城派不是人人都得会细水剑法,在我青城派多的是废物学不会细水剑法。”
说完饶有趣味的看着杜寒桥。
这时杜寒桥慢吞吞的站起身来,从桌角将自己的佩剑拿了起来,看了看张伦宿,说:“赶紧的!亮你的剑吧。”
张伦宿哑然失笑,说:“杜二公子这是做什么?”
杜寒桥直接将剑从剑鞘里抽了出来,说:“你还是不是我西北男儿?如此话多,你今天来就是想打架的,不是吗?别说那么多!”
张伦宿一声好,从背后抽出剑来,说:“咱就隔着桌子来几招,点到为止如何?”
杜寒桥说了句“随你”。瞬间剑光乍起。
杜寒桥手中的剑似幻化成几道光射向了张伦宿,但见张伦宿手中之剑一片柔光,便似小桥流水一般,那几道光好似落入溪水中的石头。
杜寒桥心中愕然,觉得自己的剑已经是眨眼间便能刺出七八剑了,可剑剑都似刺进了虚空中,每一剑都快到张伦宿无法拿剑格挡,但偏偏张伦宿随便挥几下,那刺出去的剑都产生了微小的偏差最终导致整个剑招变的剑剑都失去了准头。自己的西云快剑便这样让这人破解了?杜寒桥不信,剑越出越快,可情况却依旧没有变化,此时张伦宿居然说话,在两人比试之时,一方还能悠然自得的说话,这表明了两人之间差距太大。
“杜二公子的剑快啊,快的比我青城山的乌龟还快。”
杜寒桥心下一片绝望,那手中一道道剑光,在对方眼里近似萤火虫吗?杜寒桥停不下来,连出了几十招西云快剑,已然觉得渐渐的要脱力了,而张伦宿依旧举重若轻的挥舞着自己的剑,轻松好似在空中画出了几道溪流,将自己的剑光全部冲走了。
“杜家公子还是收了剑吧,这样下去你会累的吐血的。真的不知沫莲原来的品味如此奇怪。”
杜寒桥双目充血,手中的剑依旧不停,此时一直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苏岸柳醒了!
一道剑光如流星从空中砸下,将两柄剑同时隔开,重击之下酒桌四分五裂,苏岸柳的剑还在剑鞘中,他还未曾亮剑,只是合着剑鞘挥出了一击而已。
杜寒桥和张伦宿同时因为这一击后退了几步,苏岸柳摸着自己的白玉剑鞘,心疼的说:“看看,仔细看看,有没有裂缝。”看了许久,才长处一口气,说:“果然没有,那波斯商人没骗我,这玉上品啊。”说完,拿斜眼看着张伦宿,说:“你很想看龙骨剑吗?”张伦宿拍了拍衣服上的木屑,说:“很想!如何?”
苏岸柳走到张伦宿面前,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了看张伦宿,然后笑着说:“求我,求求我,我就给你看。”张伦宿哪曾料到,眼前这个面相气度都不凡的年轻人,居然如此泼皮。
咬着牙不知如何说,苏岸柳撇撇嘴,扭头走到还在发愣的杜寒桥身旁,搂着他的肩膀说:“公子回家啦。”说着硬拉着杜寒桥走了出去,只留下张伦宿还在想着刚才苏岸柳那暴然的一击,他从未遇见能一击将自己剑气布置出的气溪一击击碎的人。这气溪便是细水剑法第一重的秘要,运气于剑,与身外之气融合,缠与剑上,越缠便越多,剑气绵柔,剑一收那绵柔之气四散,便可布置出一道缓缓流向前方的气,可减缓对方的剑气,此招他屡试不爽,往往对手最终都会被拖进气流之中不能自拔,最后力竭而亡。本来看着杜寒桥就要如此败落在自己的剑下,哪曾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在他还在思量如果真的和苏岸柳对战有几多把握,是不是西云城所有的龙骨剑士都有如此实力时,苏岸柳又突然回来了。
“喂,那个那个,马沫莲的男人。”说着苏岸柳指了指满地的木屑接着说:“这桌子你记得赔给此楼的老板啊。”说完不等张伦宿说话,转身跑了。
张伦宿气的大骂:“无赖,泼皮。”
在回杜府的路上,石阶两旁的商铺已然都已关门。只有月光照着青石路,苏岸柳看不太清杜寒桥的脸,不知他现在何种表情,但他知道要强的杜家公子,肯定为他和张伦宿之间实力的差距感到沮丧,这沮丧到底到何地步,他也不知晓。但他不知说什么,杜家公子是不会听别人安慰的。这样弱者的行为,在强硬的杜寒桥那里是没有用的。
所以两人一路无话,到了杜府正门时,杜寒桥突然问苏岸柳:“我一直不曾和你比试过,也没有和任何一个龙骨剑士比试过,因为你们不会和我比试,你说,这个张伦宿的实力,比之你如何?如果你们面对面真真比一场如何?说实话!”
苏岸柳看了看杜寒桥,在正门悬挂的灯笼下,杜寒桥的脸色苍白的吓人。
“如果不像我今天这样突然一击破掉他的剑意,而是面对面真真打一场,估计胜负也就在一念之间,谁赢谁负,说不准。”
杜寒桥哦了一声,心里想:“原来这就是龙骨剑士的实力。原来我和龙骨剑士的差距这么大。”
末了杜寒桥拍了拍苏岸柳的肩膀说:“谢了,我回去睡了。”说完转身进了杜府,朝着自己的居所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