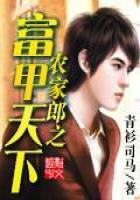陈翔刚赶到医院门口,老王头的车已经来了,整个皮卡车除了前面都坐满了人,除了小勇、大牙仔和两个被咬的工友,后车斗还带来了他同村两位工友,大家都下了车,几个把薛矮子和吴黑哥扶下车了。
他一见薛矮子和吴黑哥脸色不好,二人的伤口都在腿上,一个在胳膊上,都肿胀起来老高的,已经处于迷糊转态。他立刻面如死灰,自己方才在梦中被腐尸吐出的蛇咬到的部位,正是两位工友被咬到的部位,娘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大牙仔一下车,就撩开他那打雷般的大嗓门喊:“医生,这里的两人快不行了,你们快来,赶快……”
他这打雷似得一喊,在寂静的深更半夜,不光整个医院都听得到,几乎周围一公里可能都听得到。别说还真管用,值班的医生护士经不起他这大嗓门的敲打,以最快的速度跑了上来,把两位伤者推进急救室。
陈翔今天因为出去处理事情,身上还带了不少的现金,幸好没把工地的款及时存到银行。他和小勇赶紧去办手续,刚办完手续,小勇说:“他们两个是被闪进工棚的白头蝰给咬了,可惜那条毒蛇一闪而逃了。”
陈翔一听,觉得有些不妙,立即问:“什么?你是自己看到的吗?还是把事给说大了?”
小勇见陈翔怀疑自己把事传神了,赶紧说:“这不是我亲眼看到的,当时乱哄哄的,我是刚才听薛矮子和吴黑哥还清醒时说得。”
他们一路说这来到急救室外,边和同来的几人一起在外候着。他们又焦急等待了半个多小时,他们终于见到了主治医生出来,他们几个赶紧围上前焦急地问:“医生,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医生显得有些神情黯然,有气无力地先摇了摇头说:“两位能挺到医院已经是奇迹了,他们是被一种极其罕见的剧毒白头蝰所咬,血清和改善微循环的药物我们都用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薛矮子和吴黑哥可是大家多年的老工友,不是同村就是隔壁村,大家一医生的话,觉得这简直比法官判死刑死得还快,几人都如遭电击般。他们齐声呼道:“什么?医生求求你再想想办法,再帮帮我们吧……”
医生不语,还是摇了摇头。陈翔这是也顾不许多,看了一下医院走廊没什么人,把办完手续费,还剩下的将近两万多的工地款全部塞到医生的手里,带着哭腔说:“医生,你再想想看还有其它办法吗?”一起来几位,也都快哭了,摇着医生的手臂:“你再想想办法……”
医生迅速的把钱推了回来,为难地说:“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你们还是准备给他们办后事吧。”他说完挣脱了大家拉着手臂,逃也似的径直走了。
他们几个以前有听说这家医院很黑,医生个个都是白衣魔王,什么钱都敢收。现在连钱都不敢收了,大家觉得已经回天无力了,给蛇咬的两位工友被彻底判了死刑,且已经执行了,几人一下都如霜打茄子般焉了。
陈翔的脸同时刷一下变白,想到几个小时前,自己若不是收手地快些,若被小白头蝰给咬了,那么自己这会也该躺着了。他暗暗心惊,立时出了一身冷汗。
他赶紧给表叔打了电话,表叔好像刚从睡梦中被吵醒,迷糊地问:“谁啊?”
陈翔沉吟了一刻,带着哭腔说:“你同村的吴黑哥和薛矮子被白头蝰给咬了,现在医院已经不行了,已经走了……”
表叔好像还未完全清醒,带着梦呓地声音问:“是翔子吗?我这不是在做噩梦吧?”
陈翔又重复了一遍,表叔这下完全清醒了,惊愕过后说:“我的老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先在医院呆着,我马上找人一起过去。”
早上,不到七点半,表叔已经带人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医院,看到已故去的两位同村工友,先是一阵沉默,眼睛闭上了一会,泪珠从眼中无声地滑落,这是跟他转战多年的弟兄。
表叔难过了一阵,还是渐渐冷静了下来,吩咐与他同村的两位工友留下,与他一起来得人一起料理逝者的后事。
而后,表叔神情黯然地说:“你们先回去吧,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不能再出乱子了,记住他们的事情,你们暂时只能说在医院休养,切莫到处瞎嚷嚷,不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陈翔一起的几个医院的失魂落魄地回到工地,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他和老王头又怕再出乱子,不顾疲惫地又带了几个工友补了工棚弄得严严实实的,又买了许多防蛇的之药在工棚周围洒上。刚开工一天,就连续走了三人,这么邪门的事情,老王头做了十几年的工程,还是从未见过,陈翔心里也是直哆嗦,他们只好让工地暂时停工一天。
下午,表叔请的律师来后,由老王头和陈翔作陪跟事故家属谈赔偿事宜。陈翔内心很希望表叔能多赔一些给事故家属,可惜他和老王头都说了不算。还好,事故家属在冷静过后,知道了此次事故纯属是意外,可能跟工地的保障不利无关,心中的怨气卸下不少。
陈翔从与事故家属们交谈中,可以听出他们的弦外之音,他们更深信这次的事故跟这块凶地的冤魂有关,想必他们听了与甘大年一起来的两个工友讲了工地的当时诡异之事,家属对老王头的那句“鬼符现,冤鬼出”深信不疑,因此家属就变得通情达理多了。
表叔虽一向抠门有方,但还有信讲理,加上家属的通情达理,到了中午时分,大家就达成了赔偿协议,家属也愿意立即移走尸体火化。整件事情总算告一段落,老王头觉得特晦气,回家的路上,还拉着陈翔到庙里烧了一炷香以求心安。陈翔觉得这一天半的事情,比干一个月的活还耗神。
晚上,好几个不知情的工友邀请他小酌几杯,他这会哪再有半点心情喝酒,只是憋着不能告诉他们有两位工友已经永远走了,他婉拒了几个工友的邀请,尽快地赶回家。
陈翔一到家门口,就遇到散步回家的房东王老师;他是已年近七旬,一向和蔼可亲。
他们一老一少时常海阔天空的聊聊,王老师一见到陈翔就笑眯眯地问道:“小陈,今天怎么回来的挺早的。”
“是啊!王老师,您散步回来啦。”陈翔有些有气无力的,猛得想起王老师是教中文的高中老师,就来了精神连忙说:“王老师啊,我有一幅古卷想请您帮忙看看行吗?”
“行啊!什么古卷?我欣赏一下倒可以,要鉴定价值可不行啊。”
“哦,不是什么名贵字画,只是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一个古卷;上面写得到底是什么符号,还是文字,我不太清楚,还想您老看看。”陈翔有了工地那些可怕的经历,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只好告诉王老师是祖传的。
他说着就引着王老师到自己房间,他在窗户前那张桌子上撑开了那幅古卷。王老师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直到他的老伴喊他吃饭,没看出什么由头来;没想到王老师对这古卷还蛮有兴趣的,摇摇了头说:“小陈,等晚饭过后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您王老师。”陈翔说着,客气的把王老师送出。
陈翔吃完饭,等了有一个小时了,王老师还没来;他相信王老师不会失约,以这样年纪的老教师,那个年代人的韧劲,该不会翻箱倒柜在查找资料吧。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听到了敲门声,赶紧打开门,把王老师引进来。果然不出他所料,王老师歉意地说:”小陈,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我刚才查了一些资料,还没找到相关的线索。”
陈翔心里很是感激王老师的认真劲,连忙说:“没关系的,让您费心啦,那您再研究一下。”
陈翔赶紧挪开椅子请王老师坐下,然后赶紧给王老师倒了杯茶。王老师一直站着没坐下,戴上老花镜,在台灯前又仔细地看了起来。
他看老大一会后,终于开腔:“小陈啊,以这幅古卷的质地来说,的确看起来有些年代了,可我很奇怪这上面的红色图案却是异常清晰。”
陈翔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那您觉得这上面究竟是字,还是画?”
王老师托了一下眼睛,微晃了一下头,说:“说它是文字,它却又像窗花和花式印章;说它图案,却看起来极有规律性,看起来又有迹可循,真是令人费解!”
陈翔微斜着头,问:“那您说它假如是文字,有可能是什么朝代的呢?”
王老师说:“若是文字,光我们中国现行使用就有四十种,虽说我们中华的汉字文明从未断层过;但从古至今难保其它少数民族文明的消亡,据说有些民族的文字极其繁复”
陈翔有点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接着问:“那您觉得最有可能是哪些少数民族的文字呢?”
王老师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小陈啊,我学识有限,这个可真把我给难住了,我有一以前的同事老魏,他是个特级教师,对古文很有研究,他也许可以给你答案。”
陈翔高兴地说:“那太好了!那您什么时候联系他呢?”
“那我明天就联系一下他,看他什么时候方便。”王老师说着,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神秘:“不过,说起这古卷,我倒想起了元丰城里,一直流传着一个神秘可怕的死亡古卷传说,不知你是否听过?”
陈翔眼中闪着好奇的光:“听这传说的名字就怪吓人的,我以前好像有当地听工友提起过,就是一直没在意听,您快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