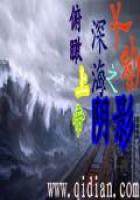在水底的阮卿竹慢慢游出通道,在更加宽阔的空间中,那压迫的感觉渐渐淡了些,加上这湖的底不深,她所处之地也能看见光亮,于是微微松了松神经的阮卿竹游速更快上几分,不一会儿便游出了水面。
露出水面的一瞬间,她大大地抽了口气,虽然双眼被那强光刺激地睁不开眼,但她还是无声笑了笑一张苍白的小脸上透出欢喜。
她出来了!
水中扑腾着,她适应了一会儿光线,渐渐地能睁开双眼,本以为是在山野外,但周遭精致的花草与华丽的宫殿却让她怔住。
借着水的浮力转了一圈,她将四周一切收入眼中,双眼狠狠一皱——这里,似乎是皇宫。
远处传来些许动静,阮卿竹耳廓一动,悄悄寻了桥底下的一处阴暗地,潜游过去,刚冒出一个头,便听闻一道男声传来,浑厚沉稳,阮卿竹双眼一变,听见数人脚步声从头顶过去。
墨景睿!
这里是皇宫?
阮卿竹一吓,呼吸不由得重了一些,头顶上的拱桥处,一身穿银铠的男子忽而眼神一转,朝底下的湖泊望去,瞧见那暗藏不寻常的水波纹时,忽而皱了眉眼。
阮卿竹还不知自己已被发现,猝不及防对上一双杀气四溢的双眼,愣在原地。
瞧见那熟悉的面容,慕云笙猛地一怔,身后黄袍加身的墨景睿见他发呆,沿他视线所望去,却只瞧见一片平静无波的湖面。
“慕爱卿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理才好?”他沉声问道,慕云笙回过神来,顿了顿,道:“臣以为此次蛮夷觐见,若为求和,自然是好事一番,只是京中防备还应慎重又慎重。”
墨景睿盯他半晌,弯了唇角道:“那这件事就交给爱卿全权处理。”
他指的,是京中防备一事。
‘全权处理’。
如何慎重的字眼,这意味着慕云笙能够掌控调派京中所有的兵权,如此举动,足以说明墨景睿对慕云笙的重用。
寻常人怕是要按耐不住跪地谢恩,慕云笙却只稍稍肃了脸色,敦厚道:“臣遵旨。”
阮卿竹藏在水底下,一直不敢出,直到一口气再无法支撑时,才静悄悄地将口鼻露出水面分毫,深吸两口。
又过了一会儿,估摸着人应走远的阮卿竹伸出头颅,果然没听见任何动静,四面八方也瞧不见宫人的身影,她松口气,正要找地方来上岸,头顶忽然银光一闪。
她抬头,对上慕云笙望来的目光,静止在水中。
“娘娘。”一声呼唤,少不了带着些许的疑惑。
阮卿竹见他没有戳穿自己的意思,低语道:“少将军。”
见阮卿竹回他,慕云笙的面容更纠结几分,顿了顿,见四周无人,他一个闪身跳下桥,头朝下地冲向湖面,却在快要入水之时,一手拍向水面,一手拉住阮卿竹的右手。
“得罪。”低语一句,他将人往上一拉,瞬息间搂住阮卿竹的肩膀,身形一转踢了一脚桥身,稳稳当当地落在桥头。
阮卿竹全身被水湿透,衣裳勾勒出她身体的曲线,带着女性的柔美,但苍白的面容上,一双乌漆墨黑的眸子却带着冷然。
慕云笙不小心扫见那白皙的脖颈,顿时目光一转,从桥头的另一头处拿过一早放在那儿的黑色披风,裹住阮卿竹的身子。
小小的身躯藏在宽大的黑披风中显得更加清瘦,那黑色披风落地,阮卿竹一动脚,才发现不知何时鞋子掉了一只。
慕云笙见她唇瓣微颤,身形哆嗦,又听远处有动静,便将人一抱,又是一句“得罪”,一黑一银两个身影瞬间消失在桥头,除了岸边那绿油油的草丛上留下的水渍,再无踪迹。
停在一间无人的宫殿中,慕云笙才松了手,一鞠躬道:“方才一时情急,还望娘娘恕罪。”
阮卿竹笑笑,见这殿中无人,才放松道:“还是本宫要多谢少将军搭救才是。”
慕云笙抬起头,见她如此神情,拧眉道:“娘娘为何突然出现在御花园中?”
御花园。
阮卿竹眼中异芒一闪,忽而意识到慕云笙这话的漏洞。
“突然?为何如此说?”她询问,见她不解的神色,慕云笙低语:“今晨卑职与大理寺少钦乌雅大人一同前去王府,为前日蒋家之事调查,此事陛下全权交给乌雅大人调查……”
越说,慕云笙便发现阮卿竹的神色愈发不对。
阮卿竹忽而冷笑一声,“原来还打着这样的主意,怪不得……”
静默半晌,阮卿竹抬头看向慕云笙,沉声道:“少将军记住,乌雅戚风此人,信不得。”
她斩钉截铁的语气让慕云笙一愣,又听她道:“可否劳烦少将军先收留本宫两日,同时,本宫还需少将军去王府中替本宫送一条消息给殿下。”
慕云笙此时才意识到不对劲之处,想起早上那个打扮精致的逸王妃,他愣愣道:“难不成王府里的那位……”
阮卿竹颔首,“是谁本宫不知,但必定是旁人假扮,绑了本宫也不知为何,总之此事幕后定有大阴谋,少将军且莫要打草惊蛇,还请先给殿下递出消息。”
阮卿竹没有将乌雅戚风的事全部说出,怀疑南川假扮王妃的事也没说,但她对慕云笙颇为信任,凭他那次冲入火场救下她的性命,便可知此人的性子定不坏,可以加以托付。
慕云笙沉思半晌,见阮卿竹煞白着一张脸,快要昏厥。
忙点头道:“如此,便请娘娘在此处稍等,卑职先去与陛下告辞,迟些会派人送来侍卫的衣裳,娘娘换上衣裳,先随臣回府。”
阮卿竹颔首,他便快步走出宫殿,扬长而去,不过半刻钟的时间,一个面容冷肃的男子走进屋来,手中还捧着一套衣裳,看见阮卿竹时也是双眼一动,显然是认出了这位逸王妃。
“娘娘且先换上衣裳,随后与属下一同出宫。”那男子低头禀告,阮卿竹接过衣裳,看着上面带有些许铠甲的衣裳,颇为沉重,不知为何就想到了通道里的那具白骨,还有那从头封到脚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