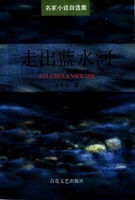一
岁月象哪吒的风火轮,掣风带火地飞转着,眨眼就转过了四个春夏秋冬。
一九四八年,在雪花般纷飞的捷报中挺胸昂首地来到了人间。
“捷报!捷报!”
在城市,在农村,在铁路,在矿山,在弹雨纷飞的战壕里;在千军万马行进的队列里;在支前队“吱扭扭”的小车声里;在翻身农民那散发着扑鼻泥土香的土地上;在国民党统治区街头巷尾的传单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听到“捷报!捷报!捷报!”
“东北我军夺得辽沈战役胜利,宣告东北全境解放。”
“华北我军打响保北、察绥战役,解放了察哈尔、绥远大部地区,太原战役正在进行。”
“西北野战军澄郃、荔北战役歼灭大量敌人,威逼西安。”
“中原野战军取得郑州战役胜利,洛阳、郑州、开封宣告解放。”
这是一个风风火火的秋天,是一个鼓舞人心、激人斗志的秋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使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御体系次第瓦解。在山东,九月下旬解放了首府济南,至此,山东全境除青岛及南部临沂这两个较大的孤城外,敌人已甚少凭借了。浓雾恶瘴被金光灿灿的太阳驱走了,解放区明朗的天空扩大了,齐鲁古国新生了。
在中原逐鹿的战场上,在战争第三个年度的头四个月里,人民解放军歼敌共达一百余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已降为二百九十万人左右。南京政府已如残秋枯叶,风雨飘摇;人民解放军欣欣向荣、军威大振,兵力迅速增到三百多万,不但质量占绝对优势,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在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进行了土地改革。翻身农民喜气洋洋,踊跃支前。
前方立功的喜讯,克敌的战报,胜利的消息,如雪片一样飞向后方。
前方在召唤,胜利在召唤。
胜利的消息,无论飞到哪里,都会令人欢欣鼓舞。然而,飞到鲁南杏花村后方医院的时候,却意外地生出了一场风波。
二
沂蒙山区的千溪百流从深壑峡谷里不息地涌流出来,经过险崮高崖,花峪明川,汇成浩浩沂河。沂河,在鲁南香峨崮前打了个弯,淌过翠柏青松荫抱的山崮,流经万树绿复的桃花峪、杏花村,飞流出山,直扑平川。
杏花村是沂蒙山区边缘的一个小村,依山靠水,村舍傍坡而落,沂水穿村而过。村里村外栽满了杏树,屋前屋后植有人们喜爱的香椿和树冠硕大的核桃树,这里环境僻静,风景秀丽,村落隐蔽,怪不得我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后方医院要选择这儿作为院址呢。
据说,阳春三月花繁时,山上山下花海一片,加上玉带似的沂河,雾乳升腾,杏花似九天降下的祥云,五彩缤纷,杏花村就掩藏在花云之中。花谢后绿叶舒生,杏花村又让树海绿波淹没了。加之高山深壑,翠峦层叠,要是没有向导,一下子很难找到这个后方医院。环境幽静、隐蔽,只是一个良好的自然条件,更主要的是这里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七十户左右的山村,参加八路军转战在外的就有三十多人。所以这是个办在人民心上的医院。病床就设在各家各户,除了医生是部队的以外,护理人员大都是本村的大嫂大娘。她们从山里采来松蘑,摸来鸟蛋,打来野雉;从河里捞来鲜鱼,捕来小虾,抓来泥鳅鳝鱼;献出黄橙橙的小米,摊出香喷喷的煎饼;来款待前方下来的伤员。她们象关怀儿女一样爱护受伤的子弟兵。
山里的村子石头当家,每个村口都竖有一块二尺高的石碑,上刻“泰山石敢当”字样,据说是为了请泰山之神镇邪,禁压不祥。独有这杏花村与众不同,村口那石头上刻的是“八路石敢当”。从这两个字的改动可以看出,杏花村破除了几千年的迷信,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能驱除兵匪盗祸,使人民翻身解放,安居乐业。不管怎么说吧,一进“石敢当”界内,处处离不得石头,石铺路、石板床,就连房顶覆盖的也是三指厚薄的大片麻青石。
村东第一家紧傍着沂河,一株老杏枝密叶繁探出围墙,柴门半开,可以望见八步宽的院子。院子中央有一张石头方桌,四下放着石磙石凳,几个战士正在听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读报。
姑娘声脆腔亮好似珠落铜盘一样悦耳。几个伤病员,有的圪蹴在石凳上卷喇叭烟,有的斜依在石墙上手支着腮帮凝神细听,有的捏着铅笔,捧着本子在记着什么。老杏树下坐了一个黑大汉,端正的脸盘上,一双鹰翅似的浓眉,仿佛要展翅飞翔,眉宇间透出兴奋的神采。
“蒋介石匪帮吹嘘为铁军之一的黄伯韬兵团,已于十一月十日晚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干净、彻底、全部消灭在碾庄一带······”
“快点!快点!”黑大个挪了挪放在腿上的拐杖,探着身子心急地对那姑娘说:“你念快点,黄伯韬逮住没有?”
“你别急嘛!下面就念到了!”姑娘善意地瞥了他一眼。
“······敌第七兵团司令黄伯韬被我击毙!”
“好!好!”
“罪有应得!”
你一言,我一语,群情象一盆炭火。有人制止说:
“同志们,先别吵吵,听听还有啥好消息!”
“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在我军强大攻势下率五十九军、七十七军战场起义······”
“嗯!这两个算识时务!”黑大汉抿了抿厚墩墩的嘴唇说。
“不许插话啦!听我继续念!”姑娘放下报纸,故作严肃地对她的病员,伤号提出警告。
黑大汉看着姑娘严肃的神情,吐了吐舌头,不再吱声了。
“这次战斗歼灭了黄伯韬的第七兵团司令部,另外有二十五军、四十四军、六十军、六十四军,一〇〇军各两个师,还有孙良诚的一〇七军两个师,五十五军、二十五军的另一个师,加上阻击打援共歼灭敌人十八个师(旅)共十七万八千余人······”
“多少?多少?”伤员们惊奇地追问。
“十七万八千余人。”
“乖乖,十八个师,咱们的陈毅司令员好胃口哇!”
“那还用说,等着吧,南边刘伯承司令员的胃口也不赖!”
“别吵!别吵!还有好消息在后头哩!”姑娘大声制止着欣喜若狂的伤病员。
“活捉第一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孙良诚,四十四军中将军长王泽濬,六十四军中将军长刘镇湘和师级军官三十多名,淮海初战,旗开得胜。”
姑娘接着念起新华社华野分社发的战斗消息来。
黑大汉默不作声地闭着眼,一反那种急躁的常态,紧紧握着那根拐杖在出神。除了可以瞥见他那凝聚的浓眉外,面色并看不出有什么感情的变化。然而他那心底却波涛翻滚,象狂风掠过大海一样。眼前出现了战场上那滚滚硝烟、闪闪火光;耳边回响着“隆隆”炮声,“哒哒”号音。激情随着对激战的忆恋而澎湃,热血伴着耳边的幻音而沸腾。前线象块巨大的磁石,捷报就象磁力线,深深地吸引着这个钢铸铁打的战士,吸引着他那颗炽热的心。
“不能再呆下去了!”他突然站起身,象挥动战刀一样把拐杖重重地砍在石板上,“喀咔!”拐杖断成二截。
他这突然的举动,把几个伤员都惊呆了,读报的姑娘也吃惊地张大嘴巴站立了起来。
“你!”姑娘撂下报纸前去扶他。
“不!”黑大汉拨开了姑娘的手臂,激动地嚷嚷,“我要上前线!”
他的话象拽着了拉火管,丝丝地燃着了每个战士心里的导火索。
“对!咱们去找院长提要求!”
“不能干瞪眼看同志们吃‘肉’!”
人们边说边呼呼拉拉往门外涌。读报的姑娘着急地在后面喊:“回来!回来!”可是谁还顾得再听她的呢!
伤员们随着黑大汉刚涌出门,迎面碰上一个人:“上哪儿去?”
这是个女同志,个不高,声不大,可轻轻的一句,便象定身符一样,把伤员们的脚后跟一下定在了原地,谁也不敢挪动了。
这个女同志姓冯名贞,别看是个年轻的姑娘,却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兵,才二十六岁,便担任了这个后方医院的副院长。她没有进过专门学校,医道却不浅,真才实学都是火线救护练出来的。她曾经在华北跟加拿大援华医疗队大夫诺尔曼bull;白求恩学习过,从老大夫那里学来了极端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论什么时候都对病员洋溢着关怀的热情,然而两根小辫却经常通过摇晃来固执地回答伤员不合理的出院要求。
自从前线传来了淮海初战告捷的喜讯,伤员们出现了异样的烦躁,女院长针对这些现象作了研究,会后要医务人员分头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她刚刚走到这一号病房,便碰见了这一群不安的战士,她一下就猜中了他们的动机和动向。
黑大汉站前一步,毫不掩饰地说:“找你给我们开通行证。”他嗓门很亮,话儿铮铮发硬。
“对!让我们出院吧!”有了领头的,大伙胆气也壮了。
女院长冯贞抬眼打量眼前这骠悍粗壮的军人,只见他端正的脸盘上泛出一层油汗,使得黑里泛红的肤色,象涂了一层油彩。一对鹰翅似的浓眉中间,聚成了黑疙瘩。看这模样,听这声音,冯贞揣度这个焦躁的勇士,已经让前线胜利的消息,炽燃得无法自制了。
“我们要上前线!”
“这里不能再呆了!”
“都快憋出神经病了!”
“不开通行证,我们自己走!”
伤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女院长吵吵,一个个活象夏天树上的知了,嚷嚷着“上前线上前线”更有那些急性子的,不管伤口好不好,甩掉拐杖,解下吊胳膊的,包头的绷带,要回去打起背包回前线。
“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能走,伤口长不好,会影响健康的。”护士姑娘着急地拦阻大家,急得眼泪往下直掉。
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中负伤转来的,也有象黑大汉那样是豫东大战后转来的重彩号。他们一听自己的部队奇兵突然出现在淮海战场,就好比在冲锋的道路上把他们拖下来一样,焦躁里夹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愤怒。
冯贞微笑着看着大家,小辫子开始在耳朵后头摆了。一边摆,一边朝院子里走去。
“副院长,你给开吧!再往下去我的心快着火啦!一分钟,不!一秒钟也不能耽搁,现在开!马上就出院。”黑大汉跟在冯贞后面焦躁地陈说着,不过与其说他是请求,倒不如说是命令,而且话语音调,使人感到能冲倒山。
女院长冯贞进了院,让大家都坐下,尽管其他伤员也一块帮腔,冯贞却毫不为动。心里话:你有千条理由,我有一定之规。她把那两根小辫左右摆了摆,笑眯眯地看着黑大汉着急。那神色好象故意罩看看男同志的火气到底能冒几丈高似的,逼视着就是不开腔,任他们说,任他们喊。
人常说:以柔克刚,这话倒真有道理。面对冯贞这和善的两盆温水似的目光,再焦躁的人也不得不收敛一下。
黑大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过火了,他克制地咽了口唾沫,复又不安地站起了身。
冯贞看见他因为焦躁而急出来的一头汗珠,便抽出自已掖在腰带一侧的毛巾给他擦去汗水,疼惜地把他按坐在石凳上。
“为什么要喊呢?”
“我······”
“想你的战马了吧?我的骑兵分队长同志?”
黑大汉默认地垂下眼皮。他思念朝夕相处的战马,更思念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
黑大汉是华东野战军长江部队骑兵大队红马分队长。他是豫东战役时负的伤,是这个医院的老病员了,安静的休养环境,对于这个性格粗犷率直得有点暴躁的勇士来说,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惩罚。他听惯了枪声、炮声,闻惯了硝烟火药,恋惯了骏马战刀,一旦处身宁静的幽雅的环境,反而觉得周身象缠了一道道棘绳一样难受。医院的药水味刺鼻,沂河的流水声刺耳,白色的绷带刺眼,山山水水都仿佛在斜着眼看他。他觉得战斗需要他,他更需要战斗。在淮海大决战到来之前,他就离开了枪炮轰鸣的战场,他觉得是一种不可宽容的罪过。要不是腿骨骨折,流血过多,在昏迷之后被支前民工担架队抬到后方来,说实在的,在他清醒的时候是无论如何不会离开部队的。如今倒好,他觉得象笼里的一只老鹰,想飞飞不起来,干看着广阔天地里那风雨雷电,而不能振翅搏击风云。
他的伤势不轻。右腿股骨骨折,经过冯贞细心诊治,也动了较为理想的手术,但为了接骨后复原愈合,还需要卧床一个阶段以配合治疗。部队首长知道他的脾气,特意亲笔留信,要他“模范守纪,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安心养伤,遵守院规,听从医院的安排。”最后特意注明,“不经医院党支部批准,不得出院。”
这封信成了冯贞对付这个脾性急躁的骑兵分队长的法宝。
黑大汉则把它看成紧箍咒,没别的办法,他只得皱着眉头,耐着性子住下来。不过他得了一种怪癖,过一会儿得揭一揭绷带,一天不知要揭多少回,医生不知要同他费多少口舌,可他总盼着纱布包裹的伤口,每一分钟都能有奇迹出现。
入院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他几次想“逃跑”,可是不知部队转战在哪里,也顾忌着大队长、政委的紧箍咒。医院也会治人的急躁病,他的伤稍能动弹一点,就给他找来差事,不是叠纱布,就是捻棉花棒,再往后干脆搬来了一架纺车。交给他纺线的任务。面对白生生的棉花,悠悠转的纺轮,他哭笑不得,一头午就把纺轮上的纱线拧断了几十回。他撂下又拾起,拾起又撂下,最后抱着纺车去伙房,要和炊事员换工。他宁肯劈满满一屋柴禾,也不愿纺一斤棉纱。
可是,任务是医院支部交下的,谁替他换工呢?没办法,只有耐着性子去干。
有一天,他打听到部队开往济南府去了,传来消息是军委批准打济南,这下一团烬火重新让春风吹燃。他扔下了纺车去请战,可是医生看了看他的伤口说:“还没好利索,不能出院。”
他憋着气回到了房东家,咬着牙练跳练跑,寻思着多活动,伤口能很快长好。没想到练过劲了,伤口又红又肿,不但没得到批准,反而挨了一顿批。为此,他捶了伤口好几下,怨恨它不争气。
济南战役打得也真够快,嘁哩咔嚓就拿下了济南城,活捉了守军司令王耀武。没多久,部队突然转移到了附近,在离医院五、六十里的山沟里扎了营。同志们都来看他,还带来了战利品。他听着胜利的消息,看着兴高采烈的战友,心中不是个好滋味,既为自己没能参加济南战役而后悔,又为战友立功受奖而欢欣。
部队在这一带整训,领导和同志们常来看望他,他反倒安下心来了,使劲地吃,使劲地睡,使劲地练,只盼着早日重回战场,纵马驰骋。
后来一连有半个月,部队没人来看他,他也打听不着消息。大家猜测大军可能南下打徐州了。他又心急火燎起来。
果不然,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刻,前方传来了捷报,传来了淮海大战初战告捷的喜讯。
胜利在召唤,黑大汉再也按捺不住了。他用掉了拐杖,踩着步子来找院长强要院长给签署出院证明。
“来!你把腿伸出来。”
黑大汉顺从地伸出了伤腿,撸起了裤腿。冯贞细心地、轻轻地捏着,摸着腿骨问:“疼吗?”
“不疼!”
“真不疼?”冯贞稍稍用力。
“不疼!不疼!真不疼!”他抽回脚,在地上重重地跺了几下,一迭连声地说“不疼!”想以此来证实伤口已彻底愈合。
冯贞那双明亮锐利的眼睛早就瞥见了他额上新渗出来的汗珠,捕捉住了他在踩脚的一瞬间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痛楚的表情。
“不疼是假的,坚持是真的。”冯贞觉得面前这个同志真够顽强的了,心动了一动,有意让他出院。但很快又被自己“要负责到底”的规定否定了。
冯贞沉吟起束,她觉得伤口已愈合,断骨已接上,但从长远考虑还是继续巩固治疗为好。她对黑大汉摆起理由来了:
“······第一,伤口刚长好,还不能作剧烈运动······”
“我有战马!”黑大汉辩解道。
“骨缝长不结实,骑马容易错位。”
“错位不怕!”黑大汉固执地说。
“你······”
“你快给我开条!”黑大汉脖梗一挺,牛劲上来了。
冯贞想摆摆理由说服他,可是他听不进去,冯贞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她非常了解,一旦被战斗的热情所燃烧,这群猛虎是关不住的。她在沉吟中决定,与军医们会诊一下,适当地批准一部分伤愈同志归队,重返前线,当然首先要研究的是这位骑兵分队长。因为她觉得他的理由可以考虑,他的无声战友是能协助他的。
黑大汉一直盼女院长说个“行”字。可是她没有张口回答他,只是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黑大汉不会蘑菇,他率直地说:“你不批准,我自己批准!”说完拉开大步要走。
冯贞笑了笑,说:“同志!你又忘了大队长和政委是怎么嘱咐你的了!”她提醒他克服急躁,恢复理智。
黑大汉没话说了,“噔噔噔”跑到自己房中,躺在铺着厚厚山草的石板床上,拉过褪色的军被蒙住了头。他大声地问自己: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