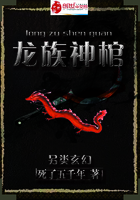我提着行囊从地道走向站台,耳边响起火车轰鸣的声音。望着四周行色匆匆的人们,我的脚步变得沉重而缓慢,寒风如刀一般从脸上呼啸刮过,我捏了捏手里的火车票,向停在站台上的列车走去。
安顿好行李,我在座位上坐了下来,顺着窗户向外眺望,想到几天之后我将在万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我的人生,心就不由得颤抖起来。曾经的沧桑、苦难、困苦与未卜的明天交叉重叠,脑海中的过去伴随着我的眼泪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叫李晓天,哈尔滨人,几天前我刚与妻子办完离婚手续,随后就踏上了这南下的征途。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可是没有办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处在急速的发展中,各种物质的需求迅猛增长,也给了很多人发家致富的机会,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下,我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也走上了这条路。经过多番思量及与家人、朋友商量后,我在县城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饲料生意。那时正是农民发展养殖业的快速增长期,对饲料的需求日渐增加,加上电视里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饲料店的生意很是红火,经营的品牌随着销量的增加也日渐增多,我又开始做起兽药代理,那也是条日进斗金的好门路。
我的饲料店就这样一直盈利了两年,但是竞争却日趋激烈,利润也随之开始下滑。我有些不满足于现状,想转行做其他生意,于是便开始酝酿另一个创业计划。
这时,一条门路摆在我面前,有朋友让我到俄罗斯去做木材生意,说白了就是倒卖木材赚取差价,将俄罗斯廉价的木材运到国内,一转手每批至少能赚到十几万。我考虑了几个晚上,和朋友约了几个老毛子谈了谈。当时中俄贸易正处于“酒肉穿肠过,合同一大摞,都说要履约,就是不过货”的阶段,大家谁都不信任谁。那几个老毛子正有一批樟子松在货场压着,听说给现金,他们高兴得嗷嗷叫,两百八一个立方就卖给了我,我把木材运回哈尔滨,转手给了一家木材厂,前后不到半个月,去掉费用,我和朋友两人各分得十七万。
初次出马就尝到了甜头,我和朋友两人凑了一百八十万大干了起来。他负责联系俄罗斯那边的木材,我则负责联系国内的下家。或许是运气偏向于我,第二笔生意赚的钱远远超过了初期的预算,于是我匆忙将饲料店交给一个同学管理,一心投到木材生意上。就这样,我的生意越做越大,财富滚雪球般源源而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俄罗斯和一位朋友闲聊时发现了一个机遇,那时俄罗斯的猪肉一斤可以卖到人民币大约二十五到三十五元,而且需求量极大。敏感的嗅觉容不得我迟缓片刻,马上联系各方人马,想尽快将这个巨大的商机把握住。
很快,我与俄罗斯一个农业联合体负责人签好了一份协议——成立一个养殖基地,俄方出场地、人力、证件等,占公司30%的股份,我方出资金占公司70%的股份。因为投入比较大,我一时间筹不到这么多钱,不得不与香港某兽药公司(我以前的合作伙伴)以及哈尔滨一家银行(当时的合作伙伴)合作。
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建后,养殖基地正式开业,但由于国内公司经常有业务需要处理,我便有些力不从心,经常是在一天之内需要同时处理每家公司的不同事务。于是,我将助理菲菲调到俄罗斯养殖基地代我管理,与她同在公司的还有我亲戚的一个朋友名叫华峰,他会说俄语,由他担任翻译。
不到一年,养殖基地开始盈利,我也轻松下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乎预料的事却发生了。
菲菲与华峰两人是养殖公司的实际掌权者,我毫无防备地把一些权力下放给了他俩。但偏偏就是这两个我最信任的人将我几年辛苦得来的一切毁于一旦。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个下午,国内贸易公司的经理告诉我说公司资金周转有些问题,需要三百五十万现金。我便与菲菲联系,叫她先把养殖公司的资金调回来应急。谁知几天后,贸易公司的财务又打电话催我尽快将三百五十万元转到贸易公司的账上,一些供应商的付款期都快到了。我本以为那天菲菲在接到我电话后就已经办了这件事,但财务却说没有。我也没想太多,于是又打电话问菲菲,她却不在公司。我便叫那里的一位副总接电话,问最近有何变化,菲菲到哪里去了?副总说没什么变化,菲菲这几天没有来公司,只说她有一些重要的事要处理,跟华峰一起走的。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是出去旅游了,可那个副总却告诉我,他俩可能是背着我搞到一起了。我将信将疑,便吩咐那个副总速到银行查账,顺便转三百五十万到国内的贸易公司。
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时间似乎过得异常缓慢,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再想更觉得问题严重了,可又无法立刻飞去俄罗斯核查,这种无形的恐慌让我不敢往最坏的结果去想。我又拿起电话打给俄罗斯的养殖公司,那副总还没有回来,只能告诉员工待副总回来马上给我电话。
漫长的等待等来的却是最坏的结果,副总从银行出来后立刻打来电话,说公司账户空了,办理人就是菲菲和华峰。突如其来的结果让我几乎瞬间崩溃,来不及去思考,根本无法接受这是真的,全身软如烂泥,只希望这是一个梦。
我应该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但最终还是拿出超越本能的毅力去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报案之后俄罗斯警方根据线索进行追查,警方从机场查到两人已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搭机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于是警方又联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警局协助抓捕疑犯。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原来布达佩斯其实是两个城市,一个是布达,一个是佩斯。等到布达佩斯的警方来电话才得知两人已在昨日出境而不知下落。
我没有精力去关心菲菲和华峰的下落,一心筹集资金将养殖公司救活,但是贸易公司已资金困难,钱远远不够。屋漏偏逢连雨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多年合作的好朋友却冷漠地拒我于千里之外。做木材生意的合作伙伴不愿意拿出资金来挽救我的养殖公司,以前围着我转的亲戚朋友也一个个消失无踪。此时,我才领悟人世间的炎凉和残忍。
我一气之下卖掉剩下的木材给我那个合作伙伴,只收了成本。但是,不管怎样努力,俄方法院还是下达执行令将公司查封了。当时如果提出诉讼保全至少需要一千万,另两家合作方此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寻求帮助。其实如果按养殖公司现状继续经营下去还是能够用利润去偿还抵押的,但是在俄罗斯,这样的机会却不可能出现。一切已成定局,养殖公司倒闭了,而我还要面对国内接二连三的诉讼。
一九九六年六月到一九九七年年底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先是老婆和我分居,带走了我那可爱的三岁的儿子和最后可能重新起步的一点资金。然后,各方债主纷纷起诉,法院查封了店面、扣押了货物、开走了车子……几次由法院出面召开的,对我进行执行的会议都因为各个债主的分配不均而作罢。我提出,各位债主是否能暂缓追债,让我继续经营,然后以利润还债。但大家多数不同意,因为每个人都想多分一点,少一点损失。到后来,由于我还不起债,就开始被拘留。
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就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直到各位债主看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同意了法院的债权分配方案,我终于解脱了。
我开始思考下一步的生计,回原单位上班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尝试去找工作,可是在当时的哈尔滨,像我这样有前科的人找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筹备南下,到广东鹏城寻找机会。
父母对我的决定很反对,但我决绝地要走,他们只能默默地给我凑了些钱,买了一张到北京的硬座车票。
正想到这里,列车开动,城市的轮廓渐渐远去,我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却只能趴在车窗上,嘴里轻轻地念着:“别了,故乡!别了,爸爸妈妈!”
我在北京转车,又在火车上熬了三天,终于进入广东境内。但等出了广州火车站才知道到鹏城要办边防证,而我没有。我又打听了一番,得知去鹏城管辖内的布吉和龙岗不用边防证,而龙岗是区政府所在地,布吉是龙岗的一个镇。按我在内地的理解,龙岗就是县城,所以我决定去龙岗碰碰运气。
我上了一辆开往龙岗的大巴,找到一个位子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半梦半醒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我的钱包被偷了”。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这才发现屁股兜已经被割了个大口子,最后的四百块钱已经不翼而飞。这让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以后在广东怎么生存呢?经过一番检查,我发现在我钱包的夹层里还有五块钱。
车到龙岗镇汽车站,我望着四周的景象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这个所谓的区政府所在地怎么这么破啊?在这里我能挣到钱吗?我看着周围背着包来打工的人,想想以后就要和他们一样去工厂站流水线,心不由得一酸。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远处开来一辆货车,上面有个胖子在喊:“谁去惠北卸橘子!两人一伙,卸一车三百块,管吃喝!”
我跳上车时足足激动几分钟,汽车在路上颠簸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才到惠州市区,这还是我自己根据四周的环境和行人的衣着来辨认的。我问胖子:“不是这里吗?大概还有多远?”
胖子说:“就快到了,一会儿到了之后你们就跟我走,我带你们到卸橘子的车皮那儿,包吃喝,还可以吃橘子。”
到了地方,我大吃一惊,本以为是到水果集散地,结果却是让我们从火车上往下卸橘子。一火车车厢的橘子我数都数不过来,至少有两千箱。我看了看正在卸货的汉子,他们就跟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般健壮。我才感觉到自己在人群中有些显眼,心里有些忐忑,一会儿千万别被赶走了啊。
胖子指着一个车厢让我过去,于是我迅速地跑到车厢旁,二话不说干了起来。
三月份的广东天就很热,没干多久,我的全身就被汗水湿透,有限的体力将我折腾得全身发软,但我依然继续坚持着从车厢内将一箱箱橘子搬到月台上的卡车上。
卸了大半夜,我已经筋疲力尽,整个人几乎要虚脱。等到胖子喊开饭的时候,我终于能歇口气了,跑到胖子那儿拿了一盒饭坐在地上就狼吞虎咽吃起来。
然后,我找了个破纸箱拆开,躺在月台上,仰望着天空,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就像家乡的儿子在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就这样,我在惠州北站干了五十多个钟头,总共卸了五车橘子,跟那些能干的人比不算多,但也不是最少的。
收工时,胖子结了一千五百块钱给我。我有点诧异,问他为什么?他笑笑说看我不像是个做苦力的人,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所以多给我一百块。
我拿到钱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这些钱对当时的我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我坐车又回到了龙岗,想想前天几乎面临绝境,于是没有找旅馆,直接到了龙岗人才市场。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不挑工作,怎么着都能找到活儿干,但进去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已经三十三岁,工厂根本不要我这个年龄的人,更何况谁看我都不像个干体力活的。其他工作要么是什么保险经纪,要不就是贸易代表,看起来就不像正经职业。几个看起来比较正规的工厂又要求员工有技术或者管理经验,而我却什么经验都没有。
我灰溜溜地从人才市场出来,心里面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和害怕,信心随之破碎。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我走到人才市场对面双龙天桥下的草坪坐下,从包里拿出刚刚在人才市场楼下买的炒米粉吃起来。吃完后我口渴得不行,很想去买瓶矿泉水,但手里攥着那点儿钱怎么也舍不得,于是跑到旁边粮食局楼下的水龙头灌了几口。
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我很想找个十元店去休息,但看到很多人都在草坪上睡觉,心想:人家能睡,我为什么不能睡?于是就这样学着他们躺在草坪上,头枕着旅行包,望着夜空,心里不胜唏嘘。想着自己就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了,怎么生存现在是毫无头绪,脑子里一片茫然。我想着这些,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哪知道,半夜里想上厕所,却发现自己的鞋子丢了。好在立交桥下的夜市还没散,我去买了双四十块钱的鞋子。唉,为省十块钱,损失得更多,又想想:人生很多时候不都是这样吗?这回睡觉小心了,把鞋子也枕到了头下。
早上,鞋子没再丢,只是衣服有些脏,需要换。我又去粮食局楼下的水龙头下把衣服洗干净,晾在立交桥下的树丛上,准备等会儿再去人才市场碰运气。
衣服很快干了,我收拾好衣服,走到对面的共青团人才市场。人才市场还没开门,很多人坐在花坛旁边,我也坐下。身边是个白净的中年人,他坐在那里拿着一份《参考消息》看得津津有味,我也有一眼没一眼地瞅着报纸上面的内容。
报纸上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软着陆”的标题吸引了我,我不由插了句嘴。显然,我的话引起了那个中年人的兴趣。他转过头有些好奇地问我:“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哪里毕业的啊?”
我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大学在东北读的,师范,学的是政治。”
他想了想,又接着问我:“那你对金融有没有兴趣?”
我感觉他话里有话,回答说:“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