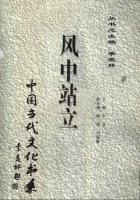除夕的思念
除夕,夜幕刚刚降下,远处的鞭炮声已开始稀稀拉拉地响起。妹妹早就抱着孩子回婆家去了。弟弟比往年还积极,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地忙着。尽管我也极力寻找往年除夕那种热烈的气氛,可内心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
“哥,摆这么多酒杯干啥?”弟妹问我。我还像往年一样,不知不觉又拿了这么多杯,在桌上摆了一圈。
端起酒杯,平时习惯致祝酒词的我,今天无话说了。看着给爹娘留的坐位,看着我给斟满的两杯酒,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尽管今天菜肴准备得很丰盛,但仍没增加我的食欲,尽管杯中斟满我平时爱喝的酒,但我仍无兴致品尝。
平时,由于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吃饭的质量和节奏常常让妻子抱怨,我早就向往春节的轻松和丰盛的佳肴。父母也体谅我们做儿女的苦衷,每年到这时候,老人都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携妻带子地回家团圆。今天我明知道父母已长眠,可我又相信父母也能回来,和我们一起过离别后的第一个年。
父母健在时,我本已体会到他们的苦心,他们那非常盼望我们回去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是多么让我感动。但是当时我却体会不到。那时我既不懂父亲临终为什么张着嘴,眼里含着最后的泪,也不懂母亲为什么病重住院,而又不愿意治,可现在想起来,我后悔,我是多么大意。娘保证知道她最后停留的日子不多了,那时,她每天都异样地看着我,不愿让我离去。她长时间细细望着我笑,忽而又偷偷擦去眼角的老泪。她愿意让我们永远陪她唠家常,可又心疼我,怕影响我第二天上班,一个劲催我早点回家睡觉。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通知我参加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会的学术年会。看着打印好的论文,我心里很矛盾。既珍惜这个机会,又舍不得离开病重的娘,担心娘不让我走,整天坐立不安。走前一天的晚饭后,娘把我叫到床前说:“你又要开会去,是吗?”我顿时明白是弟弟告诉了她。她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孩子呀,你去吧,娘一辈子就盼着你出息,你能有今天,可千万别忘了过去呀……”一句话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娘为了给我买一本书,就把攒着用来换盐吃的鸡蛋卖了,娘宁可自己不吃不穿地供我买书……想到这,我忍不住地掉下了眼泪。娘说:“去吧,收拾收拾走吧,我一定等你回来。”我迟迟不愿离开娘,想再多看娘一眼。“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呀!”娘点了点头,苦笑着,我一狠心,拔腿往外走,突然,娘喊住我,青紫的嘴唇抖着,老泪横流地说:“我怕……再也看不见你了……”一向不当人面掉泪的我,止不住失声地哭了,娘擦去眼泪说:“你哭啥,还不快回去准备准备。”
开会回来时,我看到戴着黑纱的弟弟,木然无语。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娘躺在那时,像睡着了一样那么安详。我顾不得满地灰尘,一下子跪下,泣不成声地说,“娘,我对不起您,我回来晚了……”
父亲生前爱喝酒,高兴时也劝母亲喝上一杯。但更多的时候是愿意看我们兄弟喝酒。看到我们喝到高兴时,他们放下筷子,乐得那么开心,那样子像所受的委屈和劳苦都得到了回报。
子夜时分,窗外的爆竹一齐鸣响,阵阵烟花升腾在铺着厚雪的北方小镇,而我家里却因父母双双在百天内去世,不能挂红灯,没有放鞭炮。可我真想让父母回来再和我们过一个团圆年和我们一起放一次鞭炮。我真想再喝一顿娘熬的稠稠的绿豆粥,我真想再吃一次爹包的大馅饺子。我真想当面向父母保证,从此来到我面前的世界,我都会珍惜。
现在,我有了职称、文凭,并且提了干,多篇论文得了奖。可我同时也深深地懂得,不论我多么努力,不论我再得到什么,却永远不能得到陪伴爹娘的机会,永远没有了爹打我而娘拦着的情景。
爸爸的那只大黄狗
爸爸喜欢狗是后来的事。记得我小时候,从同学家要只小狗回来,爸爸说什么也不让我养。他说:“又招跳蚤,又费粮食,养它有啥用?”
爸爸退休后,却一反常态,对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突然养起狗来。
一次大妹妹把家里养的那条大黄狗领了回来,爸爸一见这条狗,就看中了:“把这狗留下吧,我养它。”
妹妹一看爸爸挺喜欢的,就答应了。
我整天在外跑,好久没回来了。一天,我下班回家后,那只大黄狗像不认识我一样,冲着我“汪汪汪”地直咬,气得我说:“丧家犬,连我都不认识了!”
听了我的训斥,那狗虽然不叫了,可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
爸爸每天早晨起来,牵着这条狗出去遛,训练它捡东西,站起来走路,它比原来乖多了。
有一次,我回家时没注意,那只黄狗真的向我扑来,把我的胳膊给咬伤了。我顺手从门后抄起把铁锹,向着那狗砍去,那狗也像知道做错了事一样,“哼哼唧唧”地躲到沙发下不出来,我气得直砍,结果把沙发砍坏了,也没有打着狗一下。
“你要狗,还是要你儿子?要狗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这充满火药味的言语,是我逼着爸爸表态。
“这狗是他的命根子!”
平时很会调解矛盾的娘,这时也心疼地照直开了腔。一边唠叨着埋怨爸爸,又一边做我的工作。
“等明天让他们领回去,不能要这条狗。”
爸爸当时虽没马上表态,我却听见他“呼哧呼哧”地一个劲喘粗气,看出来他老人家当时心里也很矛盾。
我后来一直不满意爸爸的这件事,一百个不理解。我心里嘀咕着,怪不得别人都说山东人倔,果然如此,我以后可不能像爸爸一样。
后来,一气之下我真的好长时间没回家。同志们劝我:“不能和老人一样,老小孩小小孩嘛!”
现在,我终于理解了爸爸当时的心境,他为了小妹妹接班,提前四年就办理病退手续了。病退后他像个旋转了一生的陀螺,突然停了下来,那种惯性还未消失。
为了打发时光,他靠着自己那积累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连帮好几家筹备了饭店,后来,都是嫌他的工资高,把他给辞了。加上弟弟妹妹都相继结婚,我工作又忙,常常不回家,母亲长年有病,看病欠下了一大笔债。他耐不住寂寞,即使喜欢静的人,也并不喜欢孤独。就这样,这条黄狗在家待了两年。
自打爸爸病重住院,母亲一天忙得也没时间喂狗,就让妹妹把狗领回去了,爸爸躺在病床上,还经常问那条黄狗怎么样了,妹妹告诉他:
“大黄狗下了七个小狗崽,可招人喜欢了。”
爸爸那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去年中秋节,爸爸没能赏完最后一次圆月,没能留下一句完整的话,匆匆地走了。几天后,妹妹回来说:
“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不吃食了,没过几天就走了。”
听了这话,我觉得这条大黄狗好像挺通人性似的,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那几只还未满月的狗崽,整天可怜地叫着,那声音撕人心肝。妹妹怕把这些小生命饿死,早晨,用一个筐头,把它们送到十字路口,过往行人谁看中了谁就抱走一个,不一会儿,就都被人家抱光了。
父母走后
父母都走了,在把我们五个抚养大后,未能尽情地享几天清福,就相继匆匆地走了。走得让人心痛,走得让人难过。
我作为长子,在外甥、侄子和侄女们面前,不光分别是他们的大伯和大舅,而在这些晚辈的心里,我又担当起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的角色。
本来,我不太喜欢小孩,可就在我父母相继离去后,我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当我看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不由得使我想起父母健在时的情景。然而,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眼前,我只能用自己的言行,来填补孩子们心里感情这一空白。
一会儿,外甥彭磊问我:“大舅,我赵强哥上学了吗?”向我打听他搬到城里的小哥哥。
一会儿,不满六岁的大侄儿赵超,又摇晃着我的胳膊,问我:“大爷,我奶奶上哪去了?我爷爷咋不来呢?”
“你奶奶爷爷都不在了。”
“上哪去了?”
“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不忍心向孩子们撒谎,可眼下跟这些孩子们又说不清,只好搪塞。
每次我回到弟弟妹妹家,他们就像招待贵客一样,孩子们见到我亲得不得了,弟弟妹妹见了我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
丰盛的午餐摆上来了,这是兄弟姊妹们表示感情的一种方式。大妹妹赵杰,一边为我斟酒,一边关切地问我:“哥,你们到那边生活习惯吗?”
“有啥不习惯的,城里的东西应有尽有,就是贵点。”
我不愿意说出内心真实的感受,想尽力掩饰我思乡的情绪,减少他们对我的思念。平时少言寡语的弟弟国清,也打开了话匣子:
“过年你们回不回来?到时提前来电话,我好去接你们。”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还定不下来。”
“哥,我给你们晒了些干菜,还采了些蘑菇,走时候带着。”
赵杰的一片心意,不光是靠朴实的语言表达,更重要的是靠她那令人钦佩的行动。
“以后我离你们远了,平时你们要互相照顾,有时间赵杰就回来看看,我有机会也会回来看你们的。来!为我们全家平安,干一杯。”
此时的我,俨然像一个长者,仿佛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一遍遍地叮咛,一句句地嘱咐,似乎显得有点唠叨,可我觉得,每句话都很有意义。
几杯酒下肚后,我在床上稍躺一会儿,听说赵杰他们要回农场了,我怕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没起来送他们。可当他们走远时,我突然感到见一次面很不容易,就又跑了出去。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想嘱咐他们几句话,可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喊了一句:“赵杰,你们赶不上车就回来!”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一句多余的话,可就是这么一句话,说完心里舒服了。喊完后我的眼窝就涨潮了。母亲活着时,每次妹妹走的时候,都是她老人家说上这么一句。无形中,在弟弟妹妹眼里,我这个当长兄的,在家里又承担起父母的责任。
当今,有人常说,活得很累,其实说得有一定道理,重要的是对自己心理的承受力所感受的,更多的是自己在可怜自己。我一天工作、学习、生活,也忙忙碌碌,无时不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常常也叹息活得很累,可就在这帮孩子在我身边玩耍时,看着他们那甜甜的笑,开心的笑,我的烦恼和疲倦顿时都烟消云散了。否则,我不会在中秋佳节这天,告别妻儿,来千里之外和他们过中秋节了。
小妹
小妹的孩子可以满地跑了,看到她家今天的一切,使我联想起昨天的一幕幕。
我家姊妹五个,小妹是最小的一个。她生在“文革”初期,长在动乱年代。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知哪来的那么多不顺,中学快毕业那年,她身上突然生出一些小红点。后来越长越大,医生诊断结果是过敏性紫癜。在当地治了很长时间,病仍不见好转,后来,只好由我这个当长兄的领着到省城去治了。
头一天晚上,为了托一个朋友帮忙,只好住在另一个转车的城市。第二天一早,为了赶火车,在早班车还没发的时候,十多里地只好步行。小妹有病本来腿疼,也只好忍着往车站走。
到了省城医院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熟人,可这个熟人是在外四,外四是专治肿瘤的。小妹住进医院后,同室的病友和不知内情的医护人员,都用同情的眼光,细细打量着小妹。
安顿下小妹后,我该返回单位上班了,也想回家找人来陪护她。那时,小妹虽然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可一个人远离家乡,又有病,心里一定不好受。临走时,我嘱咐她:“要好好照顾自己,我回去马上就让家里来人陪你。”
听了这些嘱咐,小妹口里虽然答应着,表情却木然。我也压抑着感情,匆匆往楼下走。突然,我好像想起来还应说几句什么,调头又往楼上走。一上楼梯,小妹倚在病房门口,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哭泣着。见此情景,我强忍着内心的不平,劝她:“哭啥,你的病会好的!”
当我再次走出大门的时候,顾不得朋友在一旁,我的泪水也止不住地落下来了。我真想躲到一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可又不愿意让小妹看到我的眼泪。至今,小妹也不会想像出我当时出门时的心情。
我和小妹相差九岁,兄妹感情却很深。在她很小的时候,娘为了挣点钱添补这个七口之家,整天到地里干活,看小妹的重担就落在我的身上了。每天娘一上班,我就把小妹哄睡了,等到小妹睡醒的时候,我就把她放到我的两腿上,小枕头放在我两脚背上,摇晃着就像一个小摇篮一样。有时一直到天黑,娘才拖着疲倦的身体,背着半麻袋猪菜赶回来。
那时候,每当我看到街上有装扮朴素大方、长得漂亮的大姑娘时,我就盼着小妹早一天长大,到那时她一定不比她们差。我这个当哥哥的脸上也一定很光彩。
今天,小妹长大了,可偏偏又摊上了这么个病。当时,尽管医生再三安慰我,可对小妹的病,心里还始终不托底,无奈,我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她祈祷。
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小妹的病终于好了,也成了家,有了小孩。孩子长得很可爱,见到我一口一个大舅地喊着,很讨人喜欢。今天,虽然我们兄妹离得很远,但愿小妹家庭永远幸福,无论到何时,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这一页,我就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在孩子面前
自从孩子懂事后,为我在家摆出一副家长式的尊严,提供了一个机会。
星期天,我和刚满11岁的儿子上街。中午时分,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又赶上客流高峰。看着开过去的一辆辆公共汽车,人在车里像沙丁鱼似的,真没有勇气挤上车。
为了上车能有个安身之处,我们拖着两条沉重的腿,硬是多跑出一站地,从始发站上车。